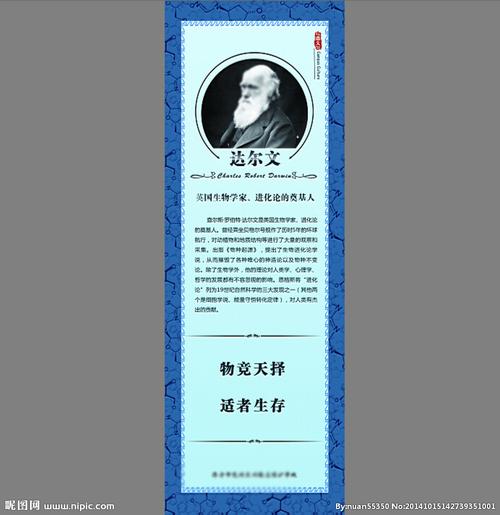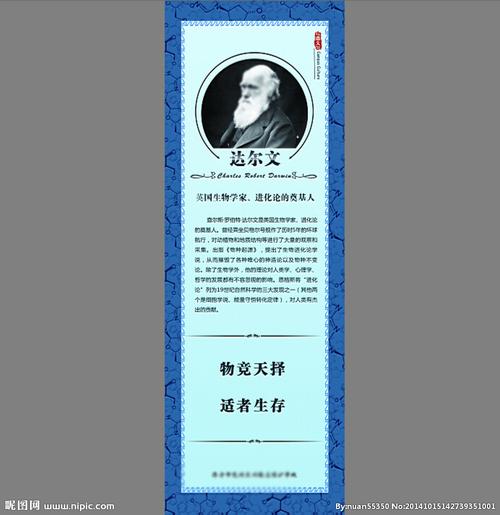
易學、樂律學、天文歷法:融通與牽合(上)
易、律、歷:融通與牽合(上)
——以《漢書·律歷志》為中心的考察與思辨
黃黎星
【內容提要】 在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史上,將易學、樂律學、天文歷法三者進行融通、關聯,構建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本文對易、律、歷形成關聯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并以易、律、歷融合的典型實例——《漢書·律歷志》為中心進行考察,并對其思想觀念、實現方法及文化意義作出分析和評判。
【關鍵詞】易學,樂律學,天文歷法,融通,牽合
作者簡介:黃黎星(1965.5—),男,福建南安人,文學博士,哲學博士后,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易學與中國古代思想文化。
(本文發表于《周易研究》2020年第二期)
律歷相關,律歷相合,是中國古代相關領域學術文化的特殊形態。從先秦時期開始,相關的論述雖然零散,卻不絕如縷,見于載籍。其標志性的典型實例,當屬《漢書·律歷志》。“律”與“歷”合為一志,始于《漢書》,影響后世。【注1】 歷代《律歷志》,保存了豐富的樂律學史、天文歷法史的資料。在從先秦至晚清的中國古代,樂律學與天文歷法兩者曾緊密聯系,相互融通。同時,在對古代律歷相關或相合這一學術文化現象進行考察時,我們不難發現:律與歷,又都與易學產生密切的關聯,也就是說,律歷相關的特色文化中,又疊加易學的參與和介入。因此,對律、歷關系進行探究時,也難以回避對易學介入其中的觀念、形態、影響的考察與辨析。【注2】
從傳世的先秦典籍中,我們尚未發現直接將易學與律、歷聯系起來的文獻資料(當然,在傳世文獻及新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文獻中,有不少將卜筮占驗與天文歷法相關聯的內容,但其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易學與天文歷數的融通)。隨著漢代易學的發展,易學之象、數、理與律、歷的聯系開始出現,并發展為頗具規模的體系,《漢書·律歷志》堪為代表。此《志》將易學作為權威經典,全面介入律、歷的學說體系中,成為易、律、歷三者結合、融通的典型實例。本文將在梳理先秦至西漢前期相關文獻資料之后,以《漢書·律歷志》作為考察的中心,評析其文本內涵,進而探究易、律、歷相聯系的思想觀念、實現方
法及得失利弊作出分析和評判。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融通”和“牽合”這兩個概念,指的是在對易、律、歷進行聯系的學說中的兩種觀念形態:融通,指易、律、歷三者的聯系彼此契合,具有原理和邏輯自洽性;牽合,指易、律、歷三者的聯系牽強附會,人為地加以類比聯系和調整湊合。以現代學科的狀況來看,易學、樂律學、天文歷法三者,學科畛域分際明晰,學科體系的屬性、所處理的對象、所面對的問題,各自獨立,不再有互相聯系、依傍的情形,自然也談不上“融通”或“牽合”。因此,本文中的“融通”和“牽合”,乃是屬于觀念上的兩種形態。
一、先秦至西漢前期律、歷關聯之發展形態考察
律、歷相關相通之觀念,起源甚古遠。學者常引的例證,首先是《尚書·舜典》中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孔傳》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寸、斛斗、斤兩皆均同。”“協時月正日”乃制定統一的天文歷法,“同律度量衡”乃以音律為基準來確定長度、體積、重量單位。丘瓊蓀先生說:“蓋在上古即已認識度、量、衡之重要性而予以統一。所有度、量、衡制皆起于律,即以律為度、量、衡制之標準法物。律者,律管也。律之長,度也;律之容,量也;律之重,權衡也;律之聲,音
高標準也。律、度、量、衡四者皆生于律,在全國范圍內予以統一,此即所謂'同’也。”《舜典》此語將“歷”與“律”并列,影響深遠,后世多引之為律、歷相關相通的最早的經典依據。
《國語·周語下》“王將鑄無射”章記載伶州鳩之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韋昭注曰:“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律聚(娶)妻而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意指律呂合于天文歷法一年十二月“月律”。歷代學者對此討論甚多,持見不一,但伶州鳩所言者,律、歷相關的意涵是明顯的。韋昭注語“陰陽相扶,律娶妻而呂生子”,乃引鄭玄易學“爻辰”說闡釋之。【注3】《國語》此章又有伶州鳩答景王問“七律者何”,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此說是將天上星宿分野的“七列”與音律的“七律”相關聯。
體現律、歷相關觀念的“十二月律”,在《禮記·月令》中已有系統對應的記載。《月令》從孟春至季冬,十二月有序排列,所作記述遵循統一的格式。今以《孟春之月》前兩段為例考察之,其文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依次解說“孟春之月”所對應的太陽運行之黃道方位,星宿之處,所配天干,當值之帝,當值之神,相應蟲物,對應之音、律、數、味、臭、祀以及祭祀品(內臟),以及'東風解凍’等物候。《孟春之月》后文還有不少內容,涉及天子居處、行止、服飾、器物,以及農耕、禮樂、祭祀、禁忌等,此不贅述。從《孟春之月》到《季冬之月》,均依此格式書寫。筆者注意的是,音、律已被系統地納入了《月令》所描繪的上據天文星相、下應物候形態,關涉對應于諸多政令人事運作規則的“宇宙圖式”中,不僅體現了律、歷相關的觀念,還為律、歷關聯到建除擇日、卜筮占驗之術形成了鋪墊。至漢易“卦氣說”象數體系,用于占驗,即與《月令》的包羅天文地理物候人事政令的龐大體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就是例證。(不過,“卦氣說”是易學對天文歷法的結合和運用,與易學介入、解說天文歷法的取向路徑有所不同。關于這方面的內容,筆者將另文論析。)
《禮記·禮運》篇中,還有直接將歷與律相類比的論述,曰:“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這里,在天地日月、陰陽五行的背景下,把天文歷數之四時十二月等,與五聲六律十二管聯系起來,這也正是律、歷相通觀念的體現。
《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其中的十二紀,各“紀”之首篇與《禮記·月令》
的內容基本相同,或即以《禮記·月令》為藍本而加以改寫,因此在歷、律關聯性觀念上,兩者相同。《呂氏春秋·仲夏紀》中的《大樂》、《侈樂》、《適音》、《古樂》,以及《季夏紀》中的《音律》、《音初》、《制樂》、《明理》諸篇,討論了音、樂、律的問題。其中,涉及到歷、律關聯的,有《大樂》及《音律》。
《大樂》篇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
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這是在“本質”與“根源”意義上闡釋音樂之產生。“生于度量”者,與《尚書·舜典》的“同律度量衡”有關聯。“本于太一”者,即本于“道”之本體。“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之語,類似《易傳》。文中提到了“日月星辰,或疾或徐”,“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源于陰陽變化,而“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雖然是由“先王定樂”,但根本上也是陰陽變化的結果。這是一種歷、律同源的觀念。
《古樂》篇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懈溪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這段記載,有黃鐘律管的尺寸數字,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特別標明時日,也是律、歷相關觀念的體現。《音律》篇曰:“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
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此所述“十二月律”,與《禮記·月令》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