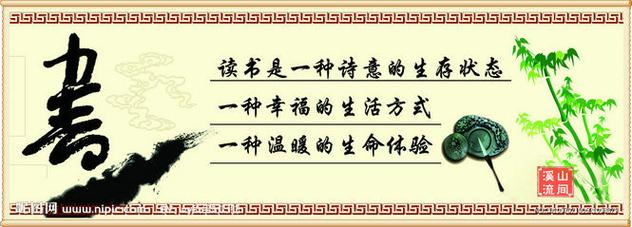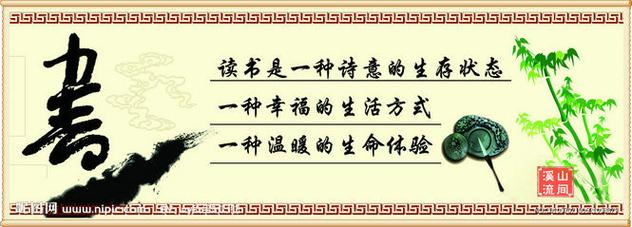
互文性理論互文性
大背景解說
作為對歷史主義和新批評的一次反撥,互文性與前者一樣,也是一種價值自由的批評實踐。這種批評實踐并不隸屬于某個特定的批評團體,而與20世紀歐洲好幾場重要的知識運動相關(guān),例如俄國形式主義、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學、馬克思主義和解構(gòu)主義。圍繞它的闡釋與討論意見,大多出自法國思想家,主要有羅蘭·巴特、朱麗婭·克里斯蒂娃、雅各·德里達、杰拉爾德·熱奈特、邁克爾·瑞法特爾。
先驅(qū)者:淵源與影響
說到互文性,法國批評家克里斯蒂娃首先回顧了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文學批評。她說,當時法國文學批評深受俄國形式主義影響,尤其是巴赫金的對話概念與狂歡理論。令她最感興趣的,則是巴赫金針對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我們知道,巴赫金提倡一種文本的互動理解。他把文本中的每一種表達,都看作是眾多聲音交叉、滲透與對話的結(jié)果。所以克里斯蒂娃說:互文性概念雖不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卻可在他的著作中推導(dǎo)出來。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中指出,獨白式歷史主義批評和文體學研究,僅僅把小說看成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或小說對于現(xiàn)實的同質(zhì)性再現(xiàn)。這種獨白批評因而無法解釋人物語言的異質(zhì)性與多樣性。它不能說明小說中各種外文學文本(extra-literarytexts)的存在,也不能充分展現(xiàn)小說語言的審美功能,即同一部小說中不同語言方式的共存交互作用,以及使用這種多元語言評價現(xiàn)實的不同方法的共存互動。巴赫金把這兩種共存互動稱之為小說的“多聲部”或“復(fù)調(diào)”現(xiàn)實,并用“文學狂歡化”來支持他的對話理論。
狂歡是一種復(fù)雜的文化形式。它原指那種包括了慶典、儀式和游藝的民間狂歡節(jié)。歐洲中世紀的狂歡節(jié),既是民眾對人生的詼諧體驗,對世界的嘻笑理解,也生動表現(xiàn)出百姓對于宗教黑暗統(tǒng)治的嘲諷態(tài)度。在此背景下,文學狂歡化專指那種產(chǎn)生于文化危機時期的復(fù)調(diào)作品或多聲部小說,巴赫金認定其主要手法是戲仿(parody)。
這類小說實乃一種互文體。它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種共時結(jié)構(gòu),偏愛把文學置于文學之外的象征性語境中。此外,它還習慣用喧鬧的方言俗語,進行各種形式的插科打諢,以便表現(xiàn)不同人群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由此造就一個擁擠雜亂的互話語(interdiscursivity)空間,創(chuàng)造一個眾聲喧嘩、卻又內(nèi)在和諧的彈性環(huán)境,從而賦予語言或意義一種不確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論時,并未預(yù)見到文學符號學的發(fā)展趨勢。可他的狂歡化概念至少暗示了在文學批評、人類學、社會學等領(lǐng)域間建立一種互文性理論的可能性。
從批評理論的角度看,對于文學文本的互動理解,其實在英美傳統(tǒng)中久已有之。18世紀初,亞歷山大·蒲伯曾在維吉爾作品中發(fā)現(xiàn)了荷馬。蒲伯確信,詩人如能善于模仿古典作品,他便能更好地模仿自然。用今天的話說,一首詩在模仿自然方面的優(yōu)劣,取決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說取決于它對前文本(pre-text)的模仿。艾略特在《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中提倡一種著名的“催化”作用。他認為,詩人精神是一種催化劑,它能改造經(jīng)驗與文學,使之變成一種新化合物。他又說,這種催化劑能消解作者和作品,促成互文性的多元化合反應(yīng),最終導(dǎo)致文學創(chuàng)作的非個性化。因此,就個人與傳統(tǒng)關(guān)系而言,傳統(tǒng)是一個同時共存的秩序。在這秩序中,先前的經(jīng)典文本一律為今人共享。每一件新作品的誕生,無疑都受到以前全部經(jīng)典的影響。也就是說,任何藝術(shù)作品都會融入過去與現(xiàn)在的系統(tǒng),必然對過去和現(xiàn)在的互文本發(fā)生作用。在此前提下,它的意義也須依據(jù)它與整個現(xiàn)存秩序的關(guān)系加以評價。
創(chuàng)作實踐方面,我們也可舉出不少例證。譬如菲爾丁的《約瑟夫·安德魯》中,人們一眼
就能看出理查遜的《帕美拉》、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乃至《圣經(jīng)》等前文本的痕跡。現(xiàn)代主義小說中,這種例子最明顯莫過于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后現(xiàn)代派作品里,首先讓人聯(lián)想到的當然是約翰·巴思。由此推開去,我們還能舉出阿多尼斯神話之于彌爾頓《利西達斯》,荷馬《奧德賽》之于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美國南方分離運動之于惠特曼1855年版的《自我之歌》,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之于華茲華斯的《序曲》,相對論之于托馬斯·品欽的小說,熱動力學之于左拉小說的影響,等等。如此奢談互文性,是否有宣揚傳統(tǒng)影響論之嫌?我們是否會在無意中抬高前文本價值,抹煞前后文本的多聲部滲透呢?
《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利用荷馬史詩的情節(jié)敷設(shè)他的篇章,并在兩個文本間確立一種肯定的(positive)互文關(guān)系。但這部小說不乏作者的自我指涉(autoreferentiality),例如《青年藝術(shù)家肖像》和《英雄史蒂芬》的影響,它因此形成了一種內(nèi)文本關(guān)系(intratexuality)。在尤利西斯的塑造上,人們也不能看到喬伊斯對荷馬人物的改造,以及他在改造這個人物時顯露出來的天才靈感,于是又出現(xiàn)一種否定的(negative)互文關(guān)系。同樣,巴思的作品不僅充斥著別人的前文本,如《堂吉訶德》,而且彌漫著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即大量引用自己以前的作品,從而把小說當作再現(xiàn)自身的世界,由此構(gòu)成一種深藏的互文性,或稱作“內(nèi)文本性”,而這正是他的后現(xiàn)代主義元小說(meta-fiction)的主要特征。
以上分析不像傳統(tǒng)影響論那樣,僅僅把文本甲與文本乙簡單聯(lián)系起來。與之相反,它把多種文本當作一個互聯(lián)網(wǎng)。它們也不像傳統(tǒng)淵源研究那樣,只把文本乙看作是文本甲直接影響的結(jié)果,而是把互文性當作文本得以產(chǎn)生的話語空間。但是我們看到,在這個空間里,無論是吸收還是破壞,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無論是自我引用還是自我指涉,文本總是與某個或某些前文本糾纏在一起。同時,讀者或批評家總能在作品中識別出文本與其特定先驅(qū)文本的交織關(guān)系。而詩人與特定先驅(qū)詩人的關(guān)系,同樣也脫離不了所謂的淵源或影響的干系。按照哈羅德·布魯姆的說法,先驅(qū)的影響,無疑造就了后來者幾乎無法克服的焦慮。
布魯姆:影響的焦慮
布魯姆在20世紀70年代集中研究“影響的焦慮”。在他看來,詩人有“強與弱”、“重要和不重要”之分。他的主要研究對象,主要是強力詩人或重要詩人。他認為,所謂強力詩人在開始創(chuàng)作時,必然和俄狄浦斯一樣,身處先弒父后娶母的境遇。就是說,詩人之于前輩的關(guān)系,或詩歌文本之于前文本的關(guān)系,也是一種愛恨交織的俄狄浦斯情結(jié)。詩人總有一種遲到感覺:重要事物已經(jīng)被人命名,重要話語早已有了表達。因此,當強力詩人面對前輩偉
大傳統(tǒng)時,他必須通過進入這個傳統(tǒng)來解除它的武裝,通過對前文本進行修正、位移和重構(gòu),來為自己的創(chuàng)造想象力開辟空間。布魯姆把這些修正功夫稱作“關(guān)系性事件”,它們可以用來衡量“兩個或更多文本間關(guān)系的修正比”。總之,這些事件構(gòu)成強力詩人創(chuàng)作時必然經(jīng)歷的6個心理階段。布魯姆從盧克萊修哲學中借用術(shù)語,分別指稱這6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