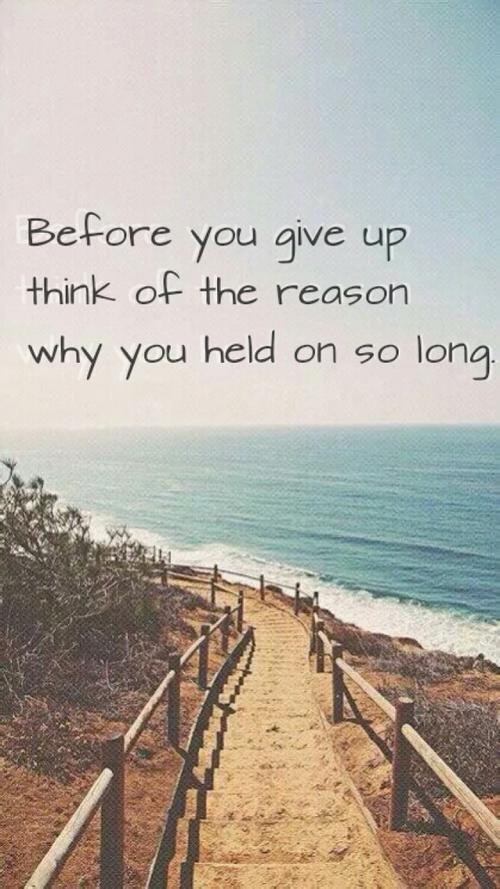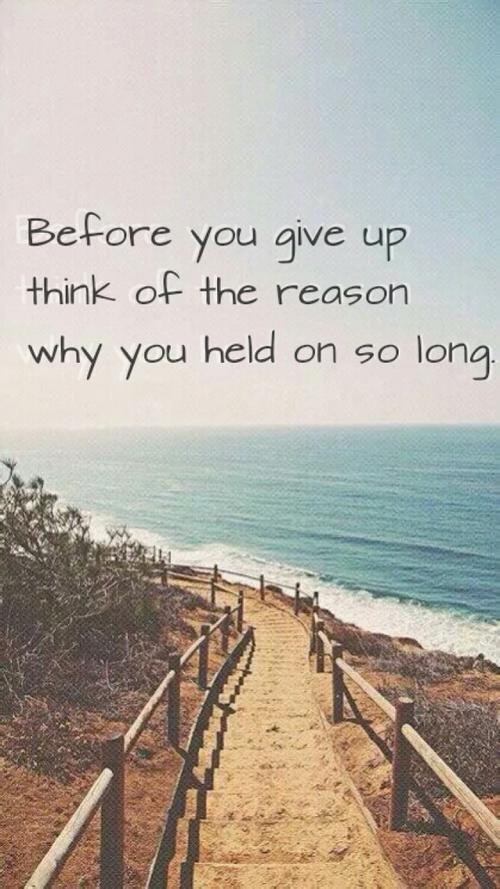
新中國十七年電影
一:政治激情——新時代背景與基本敘事類型
新中國前十七年電影總的美學特點表現為:濃郁強烈的政治意識、昂揚樂觀的精神氣質、傾向鮮明的視聽語言和通俗平易的敘事風格。其核心是政治與藝術的關系,從總體上講,藝術是圍繞著政治使命展開并服務于此的。今天對此,既應看到這一時期中國電影所帶有的明顯的時代局限性(如政治功利主義、宣傳教化色彩、藝術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等),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其產生在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必然性,并將其作為一種典型的藝術文本,在不存任何先驗偏見的基礎上,探討其藝術上的獨特處。因為其與政治有著密切聯系而一味貶抑,或因為個別作品的成功而不加分析地過高贊譽這一時期的電影都將是片面的。歷史已經拉開了一定距離,今天應該可以用更為理性客觀的角度對這一時期的中國電影進行藝術分析。
新中國電影在美學風格上與此前的中國電影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區別。
首先,在電影的藝術性質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娛樂為主體轉變為宣傳教化,這主要是由于服務對象和服務目的的改變決定的。新中國建立后,政府提出了電影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電影觀眾成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工農成了觀影主體。電影的表現和服務對象也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反映工農兵生活、服務于工農兵觀眾成了新中國電影創作的主要任務,城市市民觀眾漸遭冷落。建國初期,電影領導
部門就明確宣稱,今后的創作將不再遷就或迎合城市市民。電影院的功能也由娛樂性而變成教育和引導民眾的課堂。毛澤東要求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
隨著電影受眾和電影服務功能的變化,新中國的電影決策者倡議建立新的電影語言體系以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建國初期,新中國的電影隊伍主要由兩方面組成:來自解放區的電影工作者思想進步,政治責任感強,但缺少必要的實際創作經驗;來自國統區的電影工作者實際創作經驗豐富,熟知觀眾的口味,并擅長拍攝符合觀眾口味的影片。這兩支隊伍的會師本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共建一個良好的電影創作局面。但事實是,來自國統區的電影工作者更多地遭到懷疑和抑制,一大批來自解放區的新人成了新中國電影的主創人員,1949年生產的新中國最早的六部影片,導演以及一切工作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的。
實際上,來自國統區的夏衍、蔡楚生、吳永剛、鄭君里等人原本都是思想進步的電影工作者,之所以他們所熟悉
的“過去上海的一套”吃不開了,是因為新中國電影的美學精神發生了根本性變革,由對既有制度的批判轉為對新興體制的維護和歌頌。
為了保障社會主義時期新的美學精神在電影領域的貫徹實施,新中國在電影體制上進行了根本性變革:
在前蘇聯電影模式的影響下,進行了全行業的國有化。1919年8月27日,列寧簽署法令,將電影的生產和發行移交給人民教育委員會,電影事業實行國有化,其特點是管理上的高度集中。列寧還在1922年強調指出: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于我們是最重要的。其主要意圖是強化電影的意識形態功能,這一論斷成為蘇聯電影的行動綱領。電影國有化帶來兩種結果:一方面保證了蘇聯電影在建國恢復時期極困難的條件下,迅速發展起來。前蘇聯電影取得的巨大成就與國家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這種國家專有的方式和過于強化的意識形態氛圍也限制了前蘇聯電影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的探索和創新,電影藝術的獨特規律性往往隨著不同時期文藝政策的變更而受到沖擊甚至被犧牲掉。新中國電影發展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類似現象。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下的中央電影局(10月1日后劃規文化部管轄)宣告成立,表明了即將成立的新政府對電影事業的高度重視。1949年11月,隨著東北電影制片廠、北平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等三廠的陸續成立,新中國的國營電影制片廠便確立了其在電影業中的主導地位。建國伊始,在上海等地還有文華、國泰、昆侖、大同等私營制片公司。政府對私營電影業起初仍較為重視和支持,私營廠在較短的時間里拍攝了一批影片,包括一些質量較高的影片。然而,由于其影片《武訓傳》、《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等因政治原因陸續受到批判,私營廠很快便開始改造并于1952年1月26日宣告終結。五十年代,國家陸續興建了八一、珠江、西安、峨眉、瀟湘、天山、廣西、內蒙古等國營電影制片廠。
電影局同時兼管制片和發行(包括電影工業)兩大系統,用行政手段和計劃經濟模式管理電影生產和發行。在創作上電影局統一規劃題材,然后交由制片廠攝制,采取的是“加工訂貨”、“按期完成”、“按期交貨”的生產方式,甚至攝制組也不是自愿組合的,攝制影片的生產組織不是以導演為中心,而是以行政領導者為中心;在發行上實行“統購統銷”、“供給式分配”的方式。制片和發行被納入全國統一計劃之下,既是國家文化建設的一部分,更是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國家建立起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1950年7月,“中央人
民政府文化部電影指導委員會”成立,其成員來自宣傳、文化、統戰、工會、教育、新聞等各部門,其初衷是為了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使電影創作盡可能地避免犯各種政策性的錯誤,然而在具體工作中則是事無巨細、統攬包管,大至題材規劃、生產計劃,小至具體對話或字幕順序,都一概過問。實際上,參與領導和監督電影事業的部門非常多,特別是掌握重要國家權力的領導人士的言論往往會決定作品的榮辱成敗,因此,新中國對電影的領導可以說是全面而又強大的,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從領導機構的角度去保證電影生產全面、準確地反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新中國的電影工作者在政治使命和藝術表現間徘徊、尋覓,努力將自我的審美沖動融入國家意識形態的整體建構中,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既實現個體的審美價值,又符合藝術的政治功用。雖然其間充滿艱辛坎坷,但還是摸索出一套中國式的充滿政治激情的電影語言系統,將政治賦予濃郁的詩情。下面是幾個較為突出的特點:
一、 成長母題
影片《青春之歌》中有這樣一個段落,共產黨員盧嘉川對陷入迷惘的女青年林道靜說:“一個木是獨木,兩個木就成了林,三個木就成了森林,到那時,狂風也吹不倒它。只要投身到集體斗爭中去,把個人命運與大眾聯系起來,那時你就不是小林,而是巨大的森林了。”盧嘉川的話使林道靜頓開茅塞,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兩個人物間的關系典型代表了這一時期新中國電影的基本敘事結構──成長母題。小說作者兼影片編劇楊沫點明了這個敘事母題的基本內涵:“一些人,他們幸運地遇到了中國共產黨,他們的景況就變得大不相同。一個人一旦有了共產主義大理想,一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大理想把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那么,他不僅思想變了,行動變了,而且精神狀態也會與從前大大不同。他會從繁瑣卑微、只為自己渺小的生存而勞瘁的狀態,變得開朗、愉快、襟懷磊落;他把個人的命運與整個民族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后,他的生命也自然變得充實、巨大起來;他從個人的小天地中跳出來了、他就不再為個人的衣食(名利)、個人的前途而擔憂,他的目光不再落到個人身上,卻落到了祖國和人民的幸福上——而他們的幸福、人民大眾的幸福也就變成了他自己最大的幸福。”1
新中國電影中的主人公許多都經歷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那樣的性格軌跡,從一個不覺悟的、孤獨的個體變得目標明確、意志堅定,并最終匯入了集體斗爭或集體事業的洪流。其中,象盧嘉川那樣的共產黨人起到了啟迪、教育、培養和同化的決定性作用。
盧嘉川與林道靜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眾關系的象征:在黑暗中苦苦掙扎的中國人民只有在共產黨的指引下,才能真正擺脫盲目,走出精神的囚牢,獲得身心的解放。其它如《紅色娘子軍》中洪長青與吳瓊花,《紅旗譜》中的賈湘農與吳老忠,《舞臺姐妹》中的江波與竺春花等都是這樣的人物關系。
二、 政治娛樂
政治與娛樂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新中國電影將二者結合了起來。這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新的觀影習慣
新中國電影是不以娛樂為目的的,但對于文化生活十分貧乏的中國人來說,看電影仍然是最主要的消閑方式。由于實際生活中,政治運動此起彼伏,政治因素滲透進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以對于充斥銀幕的政治內容也便習以為常、安之若素了。而且,由于不斷受到浸染,人們也便養成了奇特的觀影方式:一種負載著強烈政治色彩的身心愉悅,將看電影視為另一種體驗政治激情的活動,并自覺地認同其政治內涵,將其作為了另一個思想教育的課堂。實際上,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特別體現在對青少年進行道德品質教育方面。
2、“政治游戲”
這里所說的“政治游戲”并無褻瀆或揶揄之意,而是指一些新中國電影將嚴肅的政治內容賦予了一種輕松詼諧的風格,產生了某種“勝似閑亭信步”的效果。這實際上也印證了毛澤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的現實生活中的政治豪情,最能代表這一特點是表現矛盾沖突中的敵方形象。雖然一些影片中也以寫實的手法展示了斗爭的殘酷性(如《南征北戰》中敵軍指揮官的形象),但更多的影片則以明顯夸張滑稽的方式調侃對手,或許敵人在外部力量上暫時占有一定優勢,但在智力、道義、精神上我方明顯占有壓倒一切的優越位置,兩相對比,益發顯現出敵人的虛弱可笑。例如,1962年拍攝的《地雷戰》,片中看不到日軍侵略的殘酷性,日軍成了在人民戰爭棋盤上被任意擺布的棋子,最后殲滅敵軍的場面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場抗日軍民輕松自如的“狩獵”活動。既然不存在我方犧牲和損失的危險,那就盡可以將之視為一次安全愜意的“游戲”。誰能忘記這個大快人心的時刻呢?鬼子兵自作聰明地開啟了我方埋設的地雷,可沾滿雙手的是污穢的糞便。哪一個中國人看了以后不會心花怒放呢?百年民族恥辱在中國人高傲的哄笑中得以洗雪,而政治的宣傳教育目的也在輕松的氛圍中得以實現。《白毛女》中的黃世仁、《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平原游擊隊》中的松井小隊長、《英雄兒女》中可笑的美國
兵、《劉三姐》中蠢笨的有產者們……都在類似的“調笑”中瞬間土崩瓦解,其虛弱內質原形畢露。
在政治氛圍濃厚的創作環境下,電影“泛政治化”了,所有的一切幾乎都是圍繞在政治意圖之下,但新中國的電影工作者鍛練出一種獨特的表現方式,雖然電影的“娛樂性”被視為了“禁區”,但他們還是努力
賦予了政治以“親近感”、“可視化”和潛在的“愉悅感”。比如,除了嚴肅的革命正劇外,電影工作者還在政治原則下,將政治主題與娛樂性很強的一些電影類型結合起來:《劉三姐》、《阿詩瑪》、《五朵金花》等展示了風光秀麗的邊疆風情和優美的民歌;《冰山上的來客》、《羊城暗哨》等融入了偵探片、恐怖片、懸疑片的敘事魅力;《平原游擊隊》、《三進山城》等借鑒了中國民間傳統的人物傳奇、故事演義等手法;當然還有《今天我休息》、《錦上添花》等喜劇化的方式,等等。實際上,也正是這些比較符合人們欣賞趣味的片子更獲得觀眾的好感。
3、新中國電影的情感表達方式
藝術作品最具魅力的重要方面便是其可以展示人類豐富細膩的情感生活,但隨著建國初期《關連長》、《武訓傳》等影片受到批判,表現“人情”、“人性”漸漸成為創作的一個“禁區”。在文藝思想上,毛澤東反對寫抽象的“人性”,而強調鮮明的階級性。他指出:“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他認為以“人性論”作為文藝理論的基礎,“是完全錯誤的”1 。因而,新中國電影中情感表現的特點是“大公無私”、“內外澄徹”、“坦蕩無遺”的集體主義和階級情誼,即使有個人化情感的揭示也必須將其納入整體秩序,歸依群體,否則便被認為是不健康的“小資情調”。《我們村里的年輕人》出現了不多見的愛情場面,然而這種愛情描寫不是建立在青年男女的相親相愛上,所有關于愛情的描寫都與他們所生活的集體緊密相連,青年人是否能贏得愛情也都與他們的勞動態度有關。所有人的愛情也都是在
勞動中建立起來的,高占武與孔淑貞、曹茂林與劉小翠、李克明與馮巧英的愛情莫不如此,年輕人完成了劈山修建水電站的任務,他們的愛情也在勞動中培養起來了。這就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產生的愛情。
小說《青春之歌》除了展示了林道靜等人的革命經歷外,也生動描繪了林道靜的情感生活,她與余永澤、盧嘉川、江華的情愛經歷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但導演崔嵬則認為:“盧嘉川與林道靜的關系,小說里寫他們或隱或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