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5日發(作者: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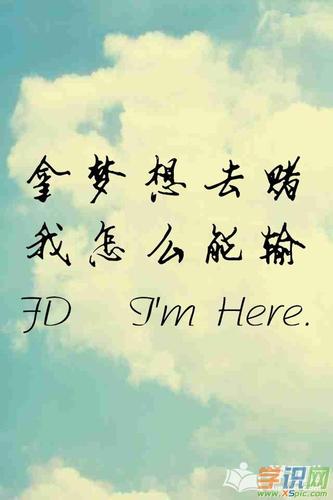
簡媜的散文3篇
把微笑還給昨天,把孤單還給自己。下面是店鋪精心為您整理的簡媜的散文,希望您喜歡!
簡媜的散文一:母者
黃昏,西天一抹殘霞,黑暗如娟蛹出穴嚙咬剩余的光,被尖齒斷頸的天空噴出黑血顏色,枯干的夏季總有一股腥。
遼闊的相思林像酷風季節涌動的黑云,中間一條石徑,四周荒無人煙。此時,晚蟬乍鳴,千只萬只,悲凄如寡婦,忽然收束,仿佛世間種種悲劇亦有終場,如我們企盼般。
木魚與小罄引導一列隊伍,近兩百人都是互不相識的平民百姓,尋常布衣遠從漁村、鄉鎮或都市不約而同匯聚在此。他們是人父、人子更多是灰發人母,隨著梵樂引導而虔誠稱誦,三步一伏跪,從身語意之所生念四句懺悔文;有的用普通話,有的閩南語,有人癡心地多念一遍。路面碎石如刀鋒,幾處凹洼仍積著雨水,相思叢林已被黑暗占據,仿佛有千條、萬條野鬼在枝椏間擺蕩、跳躍,嘲諷多情的晚蟬、訕笑這群匍匐的人們。
往前兩里山腰有一簡陋小寺,寺后巖縫流泉,據云在此苦修二十余載的老僧于圓寂前,曾加持這口活泉,愿它生生不息澆灌為惡疾所苦的人,愿一瓢冷泉安慰正在浴火的蒼生。當她荷月而歸,一襲黑長衫隱入相思林小徑,是否曾回眸遠眺山下的萬家燈火?蟬聲凄切,她的心與世間合流,她痛他們所痛的。那一夜,是否如此時,風不動,星月不動?
兩里似兩千般漫長,身旁的他肅穆凝重,黑暗中很難辨識碎石散布的方位,幾度讓她顛躓不起。她合掌稱誦、跪伏,我忽然聽到她自作主張在最后一句懺悔文加上女兒的名字,聽來像代她懺悔,又像一個平凡母親因無力醫治女兒疾病,自覺失責向蒼天告罪!她牽袖抹去涕淚,繼續合掌稱誦、三步一跪拜,謹慎地壓抑泣聲,深怕驚擾他人禱告。她生平最怕舟車,途中四小時車程已嘔吐兩次,此時一張臉青白枯槁,身子仍在微微顫抖。我悄言問她:歇一會兒好嗎?她抿緊嘴唇用力搖頭,繼續合掌稱誦觀世音,跪拜,噙淚念著“一切我今皆懺悔”。白發覆蓋下凹陷的眼睛,如一口活泉。
若不是愛已醫治不了所愛的,白發蒼蒼的老母親,你何苦下跪!
然而,我只是傾聽晚蟬悲歌,心無所求,因一切不可企求。獨自從隊伍中走出,坐在路過石頭上。微風開始格落相思花,三朵、五朵,沾著朝山徒眾的衣背,也落在我頭上。從我腳邊經過,這列跪伏隊伍肅穆且卑微,蟬歌與誦唱交鳴的聲音令我冰冷,仿佛置身無涯雪地,觀看一滴滴黑血流過。又有幾朵相思花落了。
我的眼睛應該追尋天空的星月,還是跪伏的她?那枯瘦的身影有一股懾人的堅毅力量,超出血肉凡軀所能負荷的,今我不敢正視、不能再靠近。她不需我來扶持,她已凝煉自己如一把閃耀寒光的劍。那么,飄落的相思花就當作有人從黑空中掉落的,拭劍之淚吧!
我甚至不能想像一個女人從什么時候開始擁有這般力量?仿佛吸納恒星之陽剛與星月的柔芒,萃取狂風暴雨并且偷竊了閃電驚雷;逐年逐月在體內累積能量,終于萌發一片沃野。那渾圓青翠的山巒蘊藏豐沛的蜜奶,寬厚的河岸平原筑著一座溫暖宮殿,等待孕育奇跡。她既然儲存了能量,更必須依循能量所來源的那套大秩序,成為其運轉的一支。她內在的沃野不隸屬于任何人也不被自己擁有,她已是日升月沉的一部分,秋霜冬雪的一部分,也是潮汐的一部分。她可以選擇永遠封鎖沃野讓能量逐漸衰竭,終于荒蕪;或停棲于欲望的短暫歡愉,拒絕接受欲望背后那套大秩序的指揮——要求她進行誘捕以啟動沃野。選擇封鎖與拒絕,等同于獨力抵抗大秩序的支配,她將無法從同性與異性族群取得有效力量以直接支援沉重的抵抗,她是宿命單兵,直到尋獲足以轉化孕育任務之事,慢慢垂下抵擋的手,安頓了一生。
然而,一旦有了愛,蝴蝶般的愛不斷在她心內展翅,就算躲藏于荒草叢仰望星空,亦能感受用熠熠繁星朝她拉引,邀她,一起完成瑰麗的星系;就算掩耳于海洋中,亦被大濤趕回沙岸,要她去種植陸地故事,好讓海洋永遠有喧嘩的理由。
蝴蝶的本能是吹吸花蜜,女人的愛亦有一種本能:采集所有美好事物自己進入想像,從自身記憶煮繭抽絲并且偷摘他人經驗之片段,想像繁殖成更豐饒的想像,織成一張華麗的密網。與其說情人的語匯支撐她進行想像,不如說是一種呼應——亙古運轉不息的大秩序暗示了她,現在,她憶起自己是日月星辰的一部分,山崩地裂的一部分,潮汐的一部分。想像帶領她到達幸福巔峰接近了絕美,遠超過現實世間所能實踐的。她隨著不可思議的溫柔而回飛,企望成為永恒的一部分;她撫觸自己的身體,仿佛看到整個宇宙已縮影在體內,他預先看見完美的秩序運作著內在沃野:河水高漲形成護河捍衛宮殿內的新主,無數異彩蝴蝶飛舞,裝飾了絢爛的天空,而甘美的蜜奶已準備自山巔奔流而下……她決定開動沃野,全然不顧另一股令人戰栗的聲音詢問:
“你愿意走上世間充滿最多痛苦的那條路?”
“你愿意自斷羽冀、套上腳鐐,終其一生成為奴隸?”
“你愿意獨立承擔一切苦厄,做一個沒有資格絕望的人?”
“你愿意舍身割肉,喂養一個可能遺棄你的人?”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成為一個母親!”她承諾。
那么,手中的相思花就當作來自遙遠夜空,不知名星子賜下的一句安慰吧!柔軟的花粒搓揉后散出淡薄香味,沒有悲的氣息,也不嗟哦,安慰只是安慰本身,就像人的眼淚最后只是眼淚,不控訴誰或懊悔什么。種種承諾,皆是火燎之路,承諾者并非不知,欲視之如歸。一個因承諾成為母親而身陷火海的女人,必定看到芒草叢下、蚊蠅盤繞的那口銅柜,上面有神的符篆:“你做了第一次選擇成為母親,現在,我給你第二次選擇也是最后一次;里頭有遺忘的果子與一杯血酒,你飲后更能學會背叛,所有在你身上盤絲的苦厄將消滅,你重新恢復完整的自己,如同從未孕育的處女。”
她會打開嗎?我仰問眾星,她會打開嗎?是的想要打開。
多年前,當我仍是懵懂的中學生寄宿親戚家,介紹所老板帶一位從南部來的女人,應征女傭。約莫三十歲像一枝瘦筍,背著布包及裝拉雜什物的白蘭洗衣粉塑膠袋。她留給我的第一印象不算好,過于拘謹仿佛懼怕什么以至于表情僵硬。她留下來了,很熟穩地進廚房——出于一種本能,無需指點即能在陌生家庭找到掃把、洗衣粉、菜刀砧板的位置。我不知道她的來歷也缺乏興趣探問,只強迫自己接受一張不會笑的臉將與我同睡一房。然而次日,我開始發現她的注意力放在那具黑色轉盤電話上,悶悶地撕著四季豆“啪噠”一折,丟入菜簍。黃昏快來了,肚子餓的時刻。我告訴她可以用電話,她靦腆地搖頭,繼續折豆子。然后,隔房的我聽到撥動轉盤的聲音,很多數字,漫長地轉動,像絞肉機,但是沒聽到講話聲;靜默的時間不像沒人接,她掛斷。廚房傳來鍋鏟聲。
當天深夜,也許凌晨了,我起來如廁,發現隔著屏風的那張床空了。我懾手懾腳在黑暗中搜尋,有一種窺伺的緊張感。最后從半掩著門的孩子房瞥見她的背影。三歲與六歲的表弟同睡雙人床上,像所有白天頑皮的男童到了夜間乖巧地酣睡;她坐在椅子上低聲吸泣,因壓抑而雙肩抖動,沒發覺躲在門后的我她輕輕撫摸孩子的腳,虛虛實實怕驚醒他;我從未在黑暗中隔著一步之遙窺伺一個陌生女人的內心,也許我的母親曾用同樣手勢在夜里撫摸我,只是從不讓我知道。當她忘情地接著表弟的一只腳,埋頭親吻他的腳板,我的心仿佛被匕首刺穿,超越經驗與年齡的一滴淚在眼眶打轉,忽然明白她真正的身分不是女傭是一個母親,一個拋下孩子離家出走的母親!沉默的電話只為了聽聽孩子的聲音。
“你雖然賜我第二次選擇的機會,然而既已選擇成為人間母者,在宇宙生息不滅的秩序面前,我身我心皆是圣壇上的牲禮,忠實于第一次的選擇,如武士以圣戰為榮耀,不管世人將視我如草芥奴隸,嘲諷我是愚癡的女人。啊!神,請收回你的鋼柜,看在我孩子的面上!”
第三天,她辭職。
眾星沉默。朝拜的人群已消失蹤影,遠處依然傳來梵音,輕輕敲打夜空以及夜空之外,更遼闊的夜空。山,似乎在梵唱中吟哦起來,眼前的碎石路被月光照軟了,看來像一匹無限延伸的白絹。我垂目靜坐,亦能照見絹上布滿使徒的足印,以身以口以意,以一切為人的尊嚴。若這絹上直豎刀林,那足印便有血跡;若是火炷,便有燎泡。清涼的晚風,我是如此懦弱從人群中脫逃,你可愿意代我吹熄她身上的火燎。
她始終不是逃兵,從守寡的那天起。為自己的選擇奮戰,像蕭蕭易水畔的荊軻。啊!路過的風,你吹拂原野,掠過城鎮,當明了男人社會里的女人是無聲的一群,而寡婦更是次等公民,除了是非多,賬單更多。她具備鋼鐵般的意志又不減溫婉善良,你不得不相信,蝴蝶與坦克可以并存于一個女人身上。然而,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命運?巨災淬煉她成為生命戰場上的悍將,還是她擁有至剛極柔的秉賦,便注定要不斷攬接巨災。她鐘愛的女兒在豆蔻年華染上惡疾,從此變成外表年輕貌美而心智行為如同一頭野獸。是的,傾聽的風,童話故事中美女的愛使野獸破除詛咒恢復人形,但是,什么樣的愛能使美女拔除窩藏在體內,那頭指揮她嚙咬衣服、尖叫嘶喊、朝每個人臉上吐沫的野獸呢?如果以往那位娟秀溫柔的美女仍有一絲清明,她會伏跪祈求世人賜她死,而野獸捂住他的口,野獸說:“我要長命百歲!”吟哦的風,悲劇來自兩難;老母親以己饑度女兒之饑、己渴度女兒之渴,一日三餐,沐浴更衣,把她喂養得強壯有力,于是嘶喊更尖銳、唾沫更豐沛、毆擊母親的臂膀愈來愈像鐵棍。你或許會怒號,何不讓她斷糧衰竭?人可能在生死決勝的戰役中.苛虐戰俘,視他人生命如草芥螻蟻,這是戰爭罪惡之處,它逼迫人成為邪魔的俘虜。然而,人衷心向往恒常的共體和諧,不忍在盛宴桌上聽到丐者喊餓,不忍輕裘華服自凍尸身旁走過。世間之所以有味,在于這眾苦匯聚的道場中,視他人災厄為己身災厄,他人之苦為自己苦楚的一部分。何況母親,她既在最初承諾成為人間母者,她的生命已服膺生生不息的規律,只有不斷孕育生、賜予生、扶養生,而喪失斷生、殺生的能力。不管她的孩子畸型弱智,被澆薄者視作瘟疫、道社群遺棄,她仍會忠貞于生生不息的母者精神,讓生命的光在孩子身上實踐。啊!垂愍的風,當她隔著紗窗搓洗衣服,看到窗內的女兒貞靜美麗一如往昔,忍不住停下工作,打開門鎖,進房想擁抱女兒,卻頓遭野獸般捶打時,你是否愿意透露第十年、還是二十年后的擁抱將會成真,屆時,年逾中年的女兒會扎扎實實抱著瘦骨嶙峋的老母,說:“媽媽,我好像做了惡夢!” 宙外,玉蘭樹與夜來香交遞散發清香,窺伺的風,你一定看到夜深人靜時刻,體內的猛獸逐漸盹睡,美女擁有短暫的清醒時光,乖順地讓母親摟著同眠,你聽到蒼老的聲音問:“還記不記得小時候教你的童謠?陪媽媽唱好不好?”蝴蝶、蝴蝶生得真美麗,蝴蝶、蝴蝶生得真美麗……
啊,飄泊的風,你終于能理解,等待寂靜之夜一只蝴蝶飛回來.是她的全部安慰了。如果有一天,她在生命盡頭用最后一把力氣帶走女兒,你是否愿意吹拂他們墳前的青草,不怒斥她是背職的母親?你愿意邀約無數異彩蝴蝶,裝飾一對母女的歌聲?當甜美的子夜,她們又唱起這首童謠。
梵音寂然,人籟止息,已到吹燈就寢時刻了。想必此時眾人圍聚泉邊,祈請佛泉。蟬,是天地間的禪者,悲憫永恒的空無;深夜聽蟬,喜也放下,悲也放下。
那年盛夏,午蟬喧嘩,一波波潲入充滿藥味的家屬休息室。有的人很快移出.意謂同時有人自加護病房送普通病房;有的人遷入,表示某人剛送入對門的加護室。這間六坪大的休息室像一面鏡子,清晰地看到人與人之間的牽絆。那對夫婦占去兩張長椅,早上我剛來時,六十多歲的外省丈夫含著牙刷一面走一面刷,五十來歲操勞過度的本省太太正在折被。家當、什物堆疊茶幾上,她喊丈夫把被子塞到柜子上頭,他才邊走邊刷,像所有嗓門很大、服從太太的老兵。他們看起來像房客了,毫無疑問,躺在加護病房的必是兒女。
這是難以理解的抵觸,父母可以為兒女打一場長期抗戰,反過來,兒女卻鮮能如此。我無意間知道是兒子,等公用電話時,她平靜如常交代對方去買一套西裝,報了足寸,若西服店沒有,殯儀館應該有,立刻去買,要準備辦了。她的卷發翻飛,衣褲皺得像梅干菜,趿著拖鞋進休息室,好像準備煮飯的媽媽打電話叫瓦斯行進一桶瓦斯而已。
近午時分,白襯衫、黑西裝送來了,她抖開襯衫似乎不甚滿意,戴上老花服鏡拆開袖子與腰身邊線,穿針引線縫了起來。做母親的最了解兒子身量,最后一套衣服更要體面才行,免得到冥府被譏為沒人疼的,讓做娘的沒面子。課誦之蟬,我瞥見茶幾上供奉一尊小小的觀音像。她咬斷線頭.又穿新線,像尋常日子里對丈夫嘮嘮叨叨柴米油鹽般說:“我們不可以說他不孝,這樣他到陰間就會被打。他才十九歲,也不是生病拖累我們,今天要死也不是他愿意的,哪里對不起我們?如果我們做他父母的,心里講他不孝,那他就會被打,不孝子會被打你知不知道!”
午窗邊冷邊熱,玻璃帶霧;虔誠的蟬,在你們合誦的往生咒中,我仿佛看見十九歲的他晃悠悠地走進來,扶著墻問:“阿母,衣服好了嗎?”
一定有甘美的處所,我們可以靠岸;讓負軛者卸下沉重之軛,惡疾皆有醫治的秘方。我們不需要在火宅中乞求甘霖.也毋需在漫飛的雪夜趕路,懇求太陽施舍一點溫熱。在那里,母者不必單獨吃苦,孩子已被所有人放牧。
微風吹拂黑暗,夜翻過一頁,是黎明還是更深沉的黑?她從石徑那頭走來,像提著戰戟的夜間武士,又像逆風而飛的蝴蝶。
掌中的相思花只剩最后一朵,隨手放入她的衣袋。
日子總會過完的,當作承諾。
簡媜的散文二:一襲舊衣
說不定是個初春,空氣中回旋著豐饒的香氣,但是有一種看不到的謹慎。站在窗口前,冷冽的氣流撲面而過,直直貫穿堂廊,自前廳窗戶出去;往左移一步,溫度似乎變暖,早粥的虛煙與魚干的鹽巴味混雜成熏人的氣流,其實早膳已經用過了,飯桌、板凳也擦拭干凈,但是那口裝粥的大鋁鍋仍在呼吸,吐露不為人知的的煩惱。然后,躡手躡腳再往左移步,從珠簾縫隙散出一股濃香,女人的胭脂粉和花露水,哼著小曲似的,在空氣中兀自舞動。母親從衣柜提出兩件同色衣服,擱在床上,我聞到樟腦丸的嗆味,像一群關了很久的小鬼,紛紛出籠呵我的癢。
不準這個,不準那個,梳辮子好呢還是扎馬尾?外婆家左邊的,是二堂舅,瘦瘦的,你看到就要叫二舅;右邊是大堂舅,比較胖;后邊有三戶,水井旁是大伯公,靠路邊是……竹籬旁是……進阿祖的房內不可以亂拿東西吃;要是忘了人,你就說我是某某的女兒,借問怎么稱呼你? 我不斷復誦這一頁口述地理與人物志,把族人的特征、稱謂擺到正確位置,動也不動。多少年后,我想起五歲腦海中的這一頁,才了解它像一本童話故事書般不切實際,媽媽忘了交代時間與空間的立體變化,譬如說,胖的大舅可能變瘦了,而瘦的二舅出海打漁了。他們根本不會守規矩乖乖待在家里讓我指認,他們圍在大稻埕,而我只能看到衣服上倒數第二顆鈕扣,或是他們手上抱著的幼兒的小屁股。
善縫紉的母親有一件毛料大衣,長度過膝,黑底紅花,好像半夜從地底冒出的新鮮小西紅柿。現在,我穿著同色的小背心跟媽媽走路。她的大衣短至臀位,下半截變成我身上的背心。那串紅色閃著寶石般光芒的項鏈圈著她的脖子,珍珠項鏈則在我項上,剛剛坐客運車時,我一直用指頭捏它,滾它,媽媽說小心別扯斷了,這是唯一的一串。
我們走的石子路有點詭異,老是聽到遙遠傳來巨大吼聲的回音,像一批妖魔鬼怪在半空中或地心層摔角。然而初春的田疇安分守己,有些插了秧,有的仍是汪汪水田。河溝淌水,一兩聲蟲動,轉頭看岸草閑閑搖曳,沒見著什么蟲。媽媽與我沉默地走著,有時我會落后幾步,撿幾粒白色小石子;我蹲下來,抬頭看穿毛料大衣的媽媽朝遠處走去的背影,愈來愈遠,好似忘了我,重新回到未婚時的兒女姿態。那一瞬間是驚懼的,她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她。初春平原彌漫著神秘的香味,更助于恢復記憶,找到隸屬,我終于出聲喊了她,等我喲!她回頭,似乎很驚訝居然沒發現我落后了那么遠,接著所有的記憶回來了,每個結了婚的農村婦女不需經過學習即能流利使用的那一套馭子語言,柔軟的斥責,聽起來很生氣其實沒有火氣的“母語”,那是一股強大的磁力,就算上百的兒童聚集在一起,那股磁力自然而然把她的孩子吸過去。我朝她跑,發現初春的天無邊無際地藍著,媽媽站在淡藍色天空底下的樣子令我記憶深刻,我后來一直想替這幅畫面找一個題目,想了很久,才同意它應該叫做“平安”。 渴了,我說。哪,快到了,已經聽到海浪聲了。原來巨大吼聲的回音是海洋發出來的。說不定剛剛她出神地走著,就是被海濤聲吸引,重新憶起童年、少女時代在海邊嬉游的情景。待我長大后,偶然從鄰人口中得知母親的娘家算是當地望族,人丁興旺,田產廣袤,而她卻斷然拒絕祖輩安排的婚事,用絕食的手法逼得家族同意,嫁到遠村一戶常常淹水的茅屋。
我知道后才揚棄少女時期的叛逆敵意,開始完完整整地尊敬她;下田耕種,燒灶煮飯的媽媽懂得愛情的,她沉默且平安,信仰著自己的愛情。我始終不明白,昔時纖弱的年輕女子從何處取得能量,膽敢與頑固的家族權威頡頏?后來憶起那條小路,穿毛料短大衣的母親癡情的朝遠方走去的背影,我似乎知道答案,她不是朝娘家聚落,我臆測那座海洋的能量,曉日與夕輝,雷雨與颶風,種種神秘不可解的自然力早已凝聚在母親身上,隨呼吸起伏,與血液同流。我漸漸理解在我手中這份創作本能來自母親,她被大洋與平原孕育,然后孕育我。
據說當阿祖把一顆金柑仔塞進我的嘴巴后,我開始很親切地與她聊天,并且慷慨地邀請她有空、不嫌棄的話到我家來坐坐。她故意考問這個初次見面的小曾孫,那么你家是哪一戶啊?我告訴她,河流如何如何彎曲,小路如何如何分岔,田野如何如何棋布,最重要的是門口上方有一條魚。
魚?母親想了很久,忽然領悟,那是水泥做的香插,早晚兩炷香謝天。
魚的家徽,屬于祖父與父親的故事,他們的猝亡也跟魚有關。感謝天,在完成誕生任務之后,才收回兩條漢子的生命。
我終于心甘情愿地在自己的信仰里安頓下來,明白土地的圣詩與悲歌必須遺傳下去,用口或文字,耕種或撒網,以尊敬與感恩的情愫。幸福,來自給予,悲痛亦然。
母親又從衣柜提出一件短大衣。大年初一,客廳里飄著一股濃郁的沉香味。臺北公寓某一層樓,住著從鄉下播遷而來的我們,神案上紅燭跳逗,福橘與貢品擺得像太平盛世。年老的母親拿著那件大衣,穿不下了,好的毛料,你在家穿也保暖的。黑色毛面閃著血淚斑斑的紅點,三十年了,穿在身上很沉,卻依舊暖。
我因此憶起古老的事,在海邊某一條小路上發生的。
簡媜的散文三:美麗的繭
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讓我保有我的繭。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做一絲一毫的思索時,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以回憶為睡榻,以悲哀為覆被,這是我唯一的美麗。曾經,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怎么回事呀?它們開得多美!我沒有忘記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悅。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教給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對于季節的忠實,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每一度春天之后,我更忠實于我所深愛的。
如今,仿佛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陣冷寒在心里,三月春風似剪刀啊!
有時,把自己交給街道,交給電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隨便坐著,有人來趕,換了一張椅子,又有人來要,最后,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這才是自己的。被注定了的,永遠便是注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強都是徒然,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不管愿不愿意。乖乖隨著安排,回到那個空間,告別繽紛的世界,告別我所深愛的,回到那個一度逃脫,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當鐵柵的聲音落下,我曉得,我再也出不去。
我含笑地躺下,攤著偷回來的記憶,一一檢點。也許,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也許,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便急著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嘗遍。很認真,也很死心塌地,一衣一衫,都還有笑聲,還有芳馨。我是要仔細收藏的,畢竟得來不易。在最貼心的衣袋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喚幾次,感覺那一絲溫暖。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落,懷抱著它們入睡,已是我唯一能做的報答。
夠了,我含笑地躺下,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麗的繭。
每天,總有一些聲音在拉扯我,拉我離開心獄,再去找一個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來。她們比我珍惜我,她們千方百計要找那把鎖結我的手銬腳鐐,那把鎖早已被我遺失。我甘愿自裁,也甘愿遺失。對一個疲憊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話都像一個個彩色的泡沫,對一個薄弱的生命,又怎能命它去鑄堅強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么就由它的性子吧!這是慷慨。
強迫一只蛹去破繭,讓它落在蜘蛛的網里,是否就是仁慈? 所有的鳥兒都以為,把魚舉在空中是一種善舉。
有時,很傻地暗示自己,去走同樣的路,買一模一樣的花,聽熟悉的聲音,遙望那窗,想像小小的燈還亮著,一衣一衫裝扮自己,以為這樣,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至少至少,閉上眼,感覺自己真的在繽紛之中。
如果,有醒不了的夢,我一定去做,
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
如果,有變不了的愛,我一定去求。
如果,如果什么都沒有,那就讓我回到宿命的泥土!這二十年的美好,都是善意的謊言,我帶著最美麗的那部分,一起化作春泥。
可是,連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膽妄求的。時間像一個無聊的守獄者,不停地對我玩著黑白牌理。空間像一座大石磨,慢慢地磨,非得把人身上的血脂榨壓竭盡,連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時,才肯利落地扔掉。世界能亙古地擁有不亂的步伐,自然有一套殘忍的守則與過濾的方式。生活是一個劊子手,刀刃上沒有明天。
面對臨暮的黃昏,想著過去。一張張可愛的臉孔,一朵朵笑聲……一分一秒年華……一些黎明,一些黑夜……一次無限溫柔生的奧妙,一次無限狠毒死的要挾。被深愛過,也深愛過,認真地哭過,也認真地求生,認真地在愛。如今呢?……人世一遭,不是要來學認真地恨,而是要來領受我所應得的一份愛。在我活著的第二十個年頭,我領受了這份贈禮,我多么興奮地去解開漂亮的結,祈禱是美麗與高貴的禮物。當一對碰碎了的晶瑩琉璃在我顫抖的手中,我能怎樣?認真地流淚,然后呢?然后怎樣?回到黑暗的空間,然后又怎樣?認真地滿足。
當鐵柵的聲音落下,我知道,我再也無法出去。
趁生命最后的余光,再仔仔細細檢視一點一滴。把鮮明生動的日子裝進,把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一言一語裝進,把生活的扉頁,撕下那頁最重最鐘愛的,也一并裝入,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讀。把自己也最后裝入,苦心在二十歲,收拾一切燦爛的結束。把微笑還給昨天,把孤單還給自己。
讓懂的人懂, 讓不懂的人不懂;
讓世界是世界,
我甘心是我的繭。

本文發布于:2023-12-05 00:35:23,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本文鏈接:http://m.newhan.cn/zhishi/a/1701707723111137.html
版權聲明:本站內容均來自互聯網,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簡媜的散文3篇.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簡媜的散文3篇.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