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6日發(fā)(作者:水果寶寶)

一、關(guān)于汪曾祺的生平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與張愛玲同歲),江蘇高郵人。汪家是一個士紳世家,祖父是清朝末期拔貢,開過藥店,作過眼科大夫。父親汪菊生是一位熟讀經(jīng)史子集的儒生,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花鳥魚蟲無所不愛。汪曾祺在氣質(zhì)、修養(yǎng)和情趣上較多地繼承了他父親的基因,從小受到正規(guī)的傳統(tǒng)教育和父親的寵愛,又聰穎過人。不僅有一個與沈從文一樣無憂無慮的小學(xué)時代,而且還有一個沈從文和張愛玲都無法相比的天真浪漫、幸福快樂的金色童年。
在家鄉(xiāng)讀完小說和初中后,考入江陰縣南普中學(xué)讀高中。1939年(19歲)從上海經(jīng)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昆明)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接觸到大量的新文學(xué)作品和國外的翻譯作品。1940年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最初創(chuàng)作的《小學(xué)校的鐘聲》和《復(fù)仇》等,主要受到弗吉尼亞?伍爾芙、阿索林、紀(jì)德和普魯斯特的意識流手法的影響,后得到當(dāng)時在西南聯(lián)大任中文系教授的著名小說家沈從文的親自指導(dǎo)。1943年畢業(yè)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當(dāng)中學(xué)教師,出版有小說集《邂逅集》。1947年(27歲)寫于上海的短篇小說《雞鴨名家》,在小說題材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等多方面都受到沈從文小說的極大影響,并顯露出自己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1948年到北平,失業(yè)半年,后經(jīng)沈從文推薦任職于歷史博物館。不久,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第四野戰(zhàn)軍工作團南下,在武漢參加文教單位的接管工作,被派到一女子中學(xué)任教。1950年又調(diào)回北京,在北京市文聯(lián)工作(1951年曾有一個短暫的時期到江西進(jìn)賢縣參加土改),1954年調(diào)至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在此期間,參加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xué)》等文藝刊物的編輯。1956年發(fā)表京劇劇本《范進(jìn)中舉》。
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到長城外張家口地區(qū)的一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研究所勞動改造。1962年,調(diào)回北京,在北京市京劇團任編劇。1963年參加京劇現(xiàn)代戲《沙家浜》(《蘆蕩火種》)的改編,同年,出版兒童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還參加了“樣板戲”《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開始創(chuàng)作。在80年代以后,進(jìn)入創(chuàng)作的高潮期,創(chuàng)作出許多描寫民國時期江南風(fēng)俗人情的小說,出版有小說集《晚飯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散文集《蒲橋集》、《孤蒲深處》、《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和文學(xué)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1987)、《汪曾祺文集》(四卷,1993)、《汪曾祺全集》(八卷,1998)等,受到很高的贊譽,曾掀起一個“汪曾祺熱”。1997年在北京病逝。
二、關(guān)于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
1.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分期
早期(1940-1948),作品不多,且變化很大。主要以《雞鴨名家》為代表,其他重要作品還有《落魄》、《老魯》等。《小學(xué)校的鐘聲》和《復(fù)仇》主要受西方意識流手法的影響,而《雞鴨名家》才方顯自己本色。有人說,汪曾祺寫《雞鴨名家》時,年僅27歲,完全稱得上是一個早熟的作家,“竟已抵達(dá)了爐火純青的藝術(shù)巔峰”,只可惜這是他早期惟一的一篇“登峰造極的杰作”。
中期(1949-1979),作品極少,且無成功之作,主要有《羊舍一夕》、《王全》、《看水》等。
晚期(1980-1997),厚積薄發(fā),佳作不斷,在他60大壽之際,形成了一個創(chuàng)作高潮期,有人因此說汪曾祺是“大器晚成”。但這個時期汪老的創(chuàng)作主要集中在1992年之前。而1992年之前的這個時期,又可分為“前三年”(1980-1983)和“后九年”(1984-1992)兩個階段。前三年成就突出,主要以《受戒》為代表,
其他重要作品還有《異秉》、《歲寒三友》、《大淖記事》、《晚飯花》、《皮鳳三楦房子》、《鑒賞家》、《八千歲》和《故里三陳》等。有人說,1980年汪曾祺60歲時寫《受戒》,轟動一時;61歲時寫《大淖記事》,傳詠四方,這兩文開創(chuàng)了“80年代中國小說新格局”。在這前三年的創(chuàng)作中,既有成功之作,也有失敗之作,如作于1980年底的《天鵝之死》和《寂寞與溫暖》。后九年創(chuàng)作數(shù)量和質(zhì)量都有所下降,主要作品有《詹大胖子》等。
在汪曾祺的晚期創(chuàng)作中,還有不少以短篇組成的“三部曲”,形成了“汪記風(fēng)俗小說”的一大奇觀,如《故里雜記》(李三?榆樹?魚)、《晚飯花》(珠子燈?晚飯花?三姊妹出嫁)、《釣人的孩子》(釣人的孩子?拾金子?航空獎券)、《小說三篇》(求雨?迷路?賣蚯蚓的人)、《故里三陳》(陳小手?陳四?陳泥鰍)、《橋邊小說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鐘?茶干)等。
2.《受戒》
1980年,汪曾祺以他的《受戒》開始了自己的文學(xué)“新生”,也開創(chuàng)了新時期文學(xué)文體自覺的先聲。
《受戒》發(fā)表于《北京文學(xué)》1980年第10期,獲1980年度“《北京文學(xué)》獎”。《受戒》描寫的主要環(huán)境是菩提庵,小說一開頭,即交待了充滿兒童情趣的“荸薺庵”名稱的來歷。“荸薺”這個世俗、卑微、充滿泥土氣息和溫馨回憶情調(diào)的意象,將佛教圣地的神秘、禁忌、陰冷沖冼掉了大半。明海當(dāng)和尚,沒有一絲宗教原因,而純粹是尋一條生路。因此,在作者筆下,荸薺庵是一個與世俗世界無本質(zhì)差異的地方。這里的大師父不叫方丈或住持,而叫“當(dāng)家的”。當(dāng)家的大師父仁山的主要任務(wù),即是料理三種賬務(wù):經(jīng)賬、租賬、債賬,類似賬房先生。二師父仁海是有家眷的人。三師父仁渡聰明、漂亮、充滿活力,他是打牌高手,“飛鐃”行家,還會唱最俗最昵的情歌。平常日子,各路生意人甚或偷雞摸狗之徒常來打牌聊天,佛寺凈土幾成娛樂場。逢年過節(jié)他們也殺豬吃肉,“殺豬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樣。”庵里惟一顯得干枯冷寂的人——老師叔普照,也以給即將升天之豬念“往生咒”的方式參與著這項殺生活動。作者還不失時機地插敘各路和尚帶著大姑娘、小熄婦私奔的故事。總之,“這個庵里無所謂清規(guī),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由此可見,小說通過描寫“受戒”,想要表現(xiàn)的卻是“不受戒”的人生理想。
《受戒》的發(fā)表,引起了人們普遍的驚奇與喟嘆。那時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還沒有從“傷痕”中脫離出來,《受戒》使人耳目一新。人們驚異地發(fā)現(xiàn)汪曾祺小說的另類風(fēng)格和別樣情趣。《受戒》所展示的散文化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完全與眾不同,讓人們恍悟“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隨著《大淖紀(jì)事》、《異秉》、《歲寒三友》、《八千歲》等一系列故鄉(xiāng)懷舊作品的相繼發(fā)表,汪曾祺那種清新雋永、生趣盎然而又樸實無華的風(fēng)俗畫描寫風(fēng)格,得到了文壇的普遍贊譽。
《受戒》是汪曾祺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不僅承接、豐富了廢名、沈從文這一支中斷已久的中國抒情小說的傳統(tǒng),而且,“從純粹文學(xué)的意義上來看,新時期文學(xué)所迸發(fā)出來的洶涌澎湃、鋪天蓋地的文學(xué)大潮,新時期文學(xué)所生發(fā)出來的持續(xù)不斷的語言反省,都源自那?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都源自那一次文學(xué)的?受戒?”(李銳語)。
小說中明子向小英子求愛的情節(jié),是汪曾祺所有小說中最直接、大膽的愛情描寫,但仍然是“發(fā)乎情,止乎禮”,含蓄而典雅。汪曾祺說自己受儒家影響比較多,由此可見一斑。其中最精彩的地方,是對小英子的腳印的描寫以及對明子求愛方式的表述,這是在其它小說中幾乎不可見的。而小說對善因寺的描寫,也是汪曾祺小說風(fēng)俗風(fēng)情描寫的一個典型例子,從中可以了解汪曾祺小說“宋人筆記”的風(fēng)格。當(dāng)然,風(fēng)俗風(fēng)情描寫與人物還是有關(guān)系的,就像作者自己說的“小說里寫風(fēng)俗,目的還是寫人”。風(fēng)俗與人的關(guān)系作者用“蜻蜓點水”的筆法一筆帶過:善因寺顯然不同于“荸薺庵”,它給人一種壓抑,但小英子無疑具有大無畏的精神,在那么莊嚴(yán)肅穆的地方,她依然大喊大叫,象征著不受羈絆的人類自然天性,象征著在自然田園中生長生
活的自然之子蓬勃的生命力。如果聯(lián)系到作者自己的坎坷經(jīng)歷,小英子也可視作是作者的化身。汪曾祺多想在厄運、坎坷面前像小英子那么無懼無畏,保持旺盛的生命本色呵,可惜,汪曾祺只能在夢中、文本中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這是對現(xiàn)實的逃避,同時,也是對現(xiàn)實委婉無奈的控訴。
小說的結(jié)尾文字用王國維先生的話來說,既是景語,又是情語。有人說是描寫明子與小英子之間的“性愛”。即使如此,少男少女之間的性,也是情的成份居多。如果只限于作“性”的理解,就局限了這段文字優(yōu)美的意象。這優(yōu)美有夢的特點、理想的色彩。這理想到底是什么?當(dāng)然不止于性。自由自在、不受拘束、順性自然、勤勞善良……,都是理想生活的色彩。這段文字只是夢的高潮,而前面所有的描寫都是不可或缺的鋪墊。然而,這卻是很久以前的一個夢。因此,盡管通篇都寫歡樂,經(jīng)結(jié)尾處這一句“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我們卻感受到《受戒》與《邊城》結(jié)尾翠翠與儺送那沒有結(jié)局的愛情同出一轍的哀婉。
3.《故里三陳》
汪曾祺的小說幾乎全是短制,文字省凈,可謂是惜墨如金,可在民情風(fēng)俗上卻毫不吝惜,往往濃墨重彩,鋪陳渲染,我們的讀者甚至評論家也多著眼于此,且津津樂道。無疑,民情風(fēng)物、地方習(xí)俗是其小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卻不是核心。文學(xué)是人學(xué),關(guān)注的是人物命運,人性本真。在那詩意的筆觸之下,表現(xiàn)的卻是普通百姓的哀樂苦悲,雖淡遠(yuǎn)卻寄寓著創(chuàng)作者的生存文化之思。發(fā)表于《人民文學(xué)》1983年第9期的《故里三陳》是汪曾祺一氣哈成的三個獨立的短篇,也正是這一方面的典型之作。
陳小手在當(dāng)?shù)乇粋髌婊⒁暈楫惾耍P(guān)鍵是因為他是為女人接生的男醫(yī)生,且有一雙小手。而這種被視為“異人”,奇特之外,更含著人們對他的鄙夷與不屑。“男人學(xué)醫(yī),誰會去學(xué)產(chǎn)科呢?都覺得這是一樁丟人沒出息的事,不屑為之。”顯然,這是一種愚昧狹隘的封建價值觀念。在當(dāng)?shù)厝四酥琳麄€中國人的意識中,男人應(yīng)“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男人為女人的生產(chǎn)分娩服務(wù),簡直讓人不可思議;再則,女人的身體及其分娩往往被人視為不潔甚至不祥,而一個大男人卻以此為職業(yè),實在令人不齒。可以說,正因為有了此種愚昧封建的價值觀念,陳小手的生活先在性地埋下了悲劇性的因子。
在封建倫理文化中,男女之防甚為嚴(yán)密,授受之親亦為忌諱,何況陳小手要在女人身上“摸來摸去”?這當(dāng)然是傳統(tǒng)禮教所無法容忍的。還有,在中國的封建文化中,男性視女性身體為自己獨有,“貞節(jié)”便是為女性設(shè)置的根本規(guī)范,如果其他男性對自己妻子有“肌膚之親”,自是做丈夫的奇恥大辱。在殘忍愚昧的團長那兒,陳小手接生后的被殺無疑是一種必然。也正因上述原因,團長殺人的理由便也充分:“我的女人,怎么能讓他摸來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許碰!這小子,太欺負(fù)人了!日他奶奶!”甚至殺人之后還覺得委屈。
陳四的命運雖沒有陳小手那樣悲慘,但其中亦深蘊著作者對人的生存的深切思考與關(guān)注。陳四所處之城,人們熱衷于賽城隍敬鬼神。“萬人空巷,傾城出觀”,規(guī)模盛大,排場隆盛,有各色節(jié)目,各種儀制,更有許多的癡男信女叩頭拜香……陳四在眾人眼中,是擅長踩高蹺表演“向榮”向大人的,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就在“向榮”這一角色的身上體現(xiàn),無論看客,還是陳四自己都極其看重這一點,而忘卻了自我瓦匠這一職業(yè),忘卻了作為主體的人的一面,甚至不知道自己主體本身所具有的人的本質(zhì)卻被抽空與異化。從這種對于鬼神的虔誠之中,我們看到了社會對生命的冷漠,而這種習(xí)俗的隆盛與浩大也就更現(xiàn)出人們的理性蒙昧之深。特別是陳四,以表演向榮、踩高蹺出色以為榮耀,甚至表演完畢,不卸裝,就登在高蹺上沿著澄子河堤趕去其它的地方表演。因為一次暴雨路滑不好走而誤事,自以為奇恥大辱,從此發(fā)誓不再踩高蹺。這里我們見到的是人的理性蒙昧導(dǎo)致的自我價值的失落而不自知的悲劇。風(fēng)習(xí)有其獨特情韻之外,也有其沉重壓抑的一面;文化給人帶來的不僅是正向的價值,而且也會給人帶來遮蔽和掩蓋。作者在陳四身上寄寓的便是人的生存與文化價值關(guān)系的深層思考。
陳泥鰍與上述兩人相比,更為平常普通。他下水救人的規(guī)矩是“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討價;在死人身上,他卻是不少要錢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公益會撈尸,是官家的事。而他要錢也是因為替人救急,扶危濟困,幫助陳五奶奶給小孫看病。顯然,汪曾祺在苦難生活中表現(xiàn)人們互相救濟,相濡以沫的善良本性,但隱在其中的卻是生活的更大哀戚。陳泥鰍“瓦罐不離井上破”的生命擔(dān)憂與焦慮,女人尸體驚現(xiàn)水上的社會慘劇,窮苦人家無藥治病的困窘,而這一切并非一兩次扶助便能救助,生存的悲劇氛圍籠罩著整個小說……
《故里三陳》所寫之人為市井小民,所敘之事亦是日常瑣事,而所描民情風(fēng)俗卻是韻味悠長,但我們透過此種風(fēng)俗深入思考之時,便會感到作者對底層人物的深切憫懷,對凡俗人生的悠長感喟。
4.汪曾祺小說的主要特點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tǒng)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tǒng)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chuàng)作上主張回到現(xiàn)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tǒng)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diào)著力運用有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shù)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
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zhì),不但在于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fā)現(xiàn),而且還在于他總是以近乎虔敬的態(tài)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tǒng)中,永遠(yuǎn)是清新得如同荷風(fēng)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fā)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nèi)在歡樂情緒是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息息相通的。《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fēng)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中。
然而,他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fā)出深沉的嘆喟。《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yè)》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苦辛”,《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quán)專制的殘暴。
當(dāng)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zhì)。《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往常僵硬刻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進(jìn)行了不無調(diào)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diào)節(jié)也頗似阿Q。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tài),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jīng)過反復(fù)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dá)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fēng)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xiàn)實主義的心理基礎(chǔ)。”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chuàng)傷?。”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是一位具有獨特氣質(zhì)的作家。他認(rèn)為,“我們當(dāng)然需要有戰(zhàn)斗性的……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悲壯、宏偉的作品”。但是,“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主流。”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一個作家的氣質(zhì)所決定的,不能勉強。他不習(xí)慣用政治群體意識觀察、表現(xiàn)生活,而是鐘情于個人的經(jīng)歷與命運,個人的性格特點、操行品德甚至個人隱私。他的作品情濃旨雅,即使是對兩性關(guān)系的描寫,也充滿詩情畫意,如《受戒》。他認(rèn)為,“美感作用也是一種教育作用”,“作家是感情的生產(chǎn)者。”他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的,如《職業(yè)》、《幽冥鐘》;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nèi)在的歡樂,如《受戒》、《大淖記事》;還有一部分作品由于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轉(zhuǎn)化出一種常有苦味的嘲謔,如《云致秋行狀》、《異秉》。而在有些作品里這三者是混在一起的,比較復(fù)雜。他對創(chuàng)作的理解、追求及其藝術(shù)實踐的成果,對認(rèn)識文學(xué)的內(nèi)部規(guī)律無疑是具有啟迪意義的。
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開了新時期小說散文化的先河。他歷來主張短篇小說應(yīng)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歌的界限。他有深厚的中國古代文學(xué)和民間文學(xué)的修養(yǎng),尤重《世說新語》、宋人筆記、桐城散文,又師承現(xiàn)代文學(xué)大師沈從文,這就使他的小說確實難同散文相區(qū)別。在新時期的小說中,他的作品可說是獨具一格的。
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特點首先在于重氣氛。他認(rèn)為在短篇小說中只要寫出了氣氛,即使不寫故事,沒有情節(jié),不直接寫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間浸透人物,因為氣氛即人物。所謂氣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緒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風(fēng)光、民情風(fēng)俗的生動描繪。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風(fēng)俗描繪,他“以為風(fēng)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chuàng)作的抒情詩。”風(fēng)俗自然地流露出一個民族的天性,作者總是從這里去尋找人物性格的源頭活水。凡與人物有關(guān)的風(fēng)俗,作者從來不吝筆墨,大筆揮灑;與人無關(guān)的風(fēng)俗,盡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
《大淖記事》花了近一半的篇幅來寫民情風(fēng)俗,寫大淖人自由恬然的天性。巧云和十一子就是這民情風(fēng)俗養(yǎng)育出的靈秀精英。他們的性格、愛情和追求愛情的方式同大淖的風(fēng)俗相和諧,致使人們很難分哪些是寫人物,哪些又是寫風(fēng)俗。風(fēng)俗即人,這是他同很多寫風(fēng)俗的作家最顯著的區(qū)別。
作品要有氣氛,還須有能夠造出氣氛的語言。汪曾祺的小說語言一方面追求生活語言的色、香、味、活、鮮,令人感到清新自然,另一方面講究文學(xué)語言的絕、妙、精、潔、雅,令人讀來韻味悠長。語言要和人物貼近,這是作家用語言造氣氛的妙訣。敘述、描寫、對話,都從人物出發(fā),盡可能用人物的語言來表達(dá)。于是寫販夫走卒之事,便多用俚俗之語;寫文人學(xué)士之事,則雜以少許文言。同是愛情,《受戒》的語言充滿小兒小女的天真童趣,《大淖記事》卻流溢著少男少女的青春詩意。
三、學(xué)習(xí)重點難點提示
1.汪曾祺的短篇小說觀和他在小說文體創(chuàng)造上的自覺意識。
在汪曾祺重新開始創(chuàng)作的20世紀(jì)80年代,是一個文學(xué)流派和文學(xué)潮流不斷興起,又不斷更替的時代,許多作家都被卷入了各種潮流之中,而汪曾祺則是少數(shù)幾位只按照自己的文學(xué)理想寫作的“潮流之外”的作家。汪曾祺與當(dāng)代大多數(shù)小說作家不同,他從不涉足長篇小說,也從來也沒想過要寫一部“史詩性”的或“全景式”的長篇作品。他在《汪曾祺自選集?自序》中說:“我只寫短篇小說,因為我只會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我只熟悉這樣一種對生活的思維方式。”
雖然我們還不能說汪曾祺主觀上想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小說文體,但是,他在“小說散文化”方面的努力卻是自覺的。正如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中所說:“我的小說的另一個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不喜歡布局嚴(yán)謹(jǐn)?shù)男≌f,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汪曾祺的小說雖然也涉及他曾生活過的昆明、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但大多仍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鄉(xiāng)的生活,既不特別設(shè)計情節(jié),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沖突,只是專注于風(fēng)俗民情的表現(xiàn),而這些風(fēng)俗民情也不是推動故事發(fā)展和人物性格變化的主要因素。因此,他的小說不但沒有較強的故事性,而且故意在要與“戲劇化小說”背道而馳,使小說呈現(xiàn)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態(tài),在“散文化”中創(chuàng)造一種生活的“詩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汪曾祺是一個有著清醒意識的文體家。
2.汪曾祺在廢名、沈從文,與阿城、賈平凹之間承前啟后的作用。
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傾向,受到廢名和沈從文的較大影響。我們在上學(xué)期關(guān)于“沈從文與?京派?文學(xué)”中曾講到,廢名作品的特別之處,是田園牧歌的情調(diào)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營造,致力于鄉(xiāng)村的風(fēng)土人情,
特別是鄉(xiāng)村的兒女情態(tài),他所寫的是“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也就是說,他不但是把小說當(dāng)作散文來寫,而且還要把散文化的小說寫成抒情詩。
沈從文的小說創(chuàng)作也較多地受到廢名的影響,一方面以“鄉(xiāng)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對現(xiàn)代文明進(jìn)行無情的諷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則立志要成為湘西生活的敘述者和歌者。因此,以廢名和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小說家,不僅在創(chuàng)作上“通過作家人生體驗的融入、散文化的結(jié)構(gòu)和筆調(diào),以及牧歌情調(diào)或地域文化氣氛的營造”,形成了“文體風(fēng)格趨于生活”的共同特點,而且,還在理論上對“戲劇化小說”進(jìn)行質(zhì)疑,反對裝假、做作和矯情,主張消除小說的戲劇化設(shè)計,特別是在故事情節(jié)上的人為結(jié)構(gòu)和人物性格上的刻意追求,恢復(fù)生活的原狀,展示生活的本色,寫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小說或“隨筆風(fēng)格的小說”。
但是,在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這一流派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隨著革命運動的風(fēng)起云涌而被人們有意無意地遺忘了。與這一流派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相近的蕭紅的《呼蘭河傳》,也無法歸入當(dāng)時的創(chuàng)作主流之中。
汪曾祺的出現(xiàn),連接上了這種被遺忘的小說風(fēng)格。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雖然短篇小說也是一種引人注目并且成績斐然的創(chuàng)作形式,但當(dāng)時的名篇,除茹志鵑的《百合花》外,大多屬于“戲劇化小說”的范疇,那些帶有一點散文化特點的短篇小說,如我們在專科階段講到的,周立波以“明遠(yuǎn)”、“悠徐”風(fēng)格寫作的《山那邊人家》,以及林斤瀾以追求“含蓄曲折”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的《趕擺》、《慚愧》等作品,都相繼受到了非議或批判。
在20世紀(jì)70年代,這一風(fēng)格的創(chuàng)作完全中斷。因此,汪曾祺的出現(xiàn),才使人們驚訝:“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汪曾祺才被人們看作是“在文學(xué)史上是具有著?承先啟后?意義的小說家”,才被人們稱為“開近年文學(xué)尋根之風(fēng)”的作家。
汪曾祺小說在文體上的創(chuàng)造,又影響著阿城、賈平凹等一些小說和散文家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特定地域的民風(fēng)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80年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最為流行的方式和觀念。汪曾祺關(guān)于“風(fēng)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chuàng)作的生活抒情詩”的觀點,對“尋根文學(xué)”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進(jìn)作用。
我們的專科教材《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在第19章“文化尋根”中說:“興起于80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xué)?,是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中帶有強烈沖擊意味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可以說是當(dāng)代文學(xué)開始向縱深發(fā)展的一個標(biāo)志性的文學(xué)運動。……在小說界,1980年汪曾祺就以他的《受戒》等一系列具有鮮明民間色彩與價值取向的文化風(fēng)俗小說給小說創(chuàng)作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1982~1983年間,王蒙發(fā)表的系列小說《在伊犁》雖然描寫的是一段個人生活的經(jīng)歷,但它對新疆各民族和伊斯蘭文化的關(guān)注,以及對生活和歷史的寬容態(tài)度,都為后來的尋根文學(xué)開了先河。1983年后,隨著賈平凹的《商州初錄》、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憶的《小鮑莊》、李杭育的《最后一個漁佬兒》等作品的發(fā)表和引起轟動,許多知青作家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了尋根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并成為這一文學(xué)潮流的主體。”
“由?尋根文學(xué)?作家創(chuàng)造出的審美形態(tài)是多種多樣的,大多表現(xiàn)了作家主體的獨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審美理想。其中,有一些作家傾向于從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尋求精神力量,以求達(dá)到對當(dāng)代生活困境的解脫和超越,這在作品中往往表現(xiàn)在對人物的刻畫上,通過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格形象表達(dá)出文化魅力,以此完成對一種人格境界的美感塑造。比如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樹王》,都直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核,棋、字、樹,都是中國文化中人格的象征,小說中的人物便在與傳統(tǒng)文化的相融中,實現(xiàn)了一種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
賈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和小說,則以陜西南部的商州地區(qū)作為背景,挖掘秦漢文化的源流,表現(xiàn)了商州在現(xiàn)代文明的時代氛圍中所經(jīng)歷的嬗變,構(gòu)成了一個具有相當(dāng)文化意蘊的獨特空間,體現(xiàn)了作家對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實境遇的關(guān)注。
3.汪曾祺小說的回憶性特點、散文化的結(jié)構(gòu)和由獨特的語氣、語調(diào)和語感形成的語言風(fēng)格。
汪曾祺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和故鄉(xiāng)高郵度過的(在北京生活了45年,在高郵生活了20年),在其他地方都不超過十年(其中,昆明7年,張家口農(nóng)科所4年,上海2年,江西進(jìn)賢數(shù)月)。而汪曾祺一生中寫得最好的作品,如《受戒》、《大淖記事》、《歲寒三友》、《異秉》、《晚飯花》、《皮鳳三楦房子》、《鑒賞家》、《八千歲》和《故里三陳》等,則都是與故鄉(xiāng)高郵有關(guān)的童年時代的生活,其次才是昆明期間的生活,再其次才是北京期間的生活,而這些生活大多也是遠(yuǎn)離現(xiàn)實的過去的生活。在汪曾祺眼中,所謂小說,就是“跟一個可以談得來的朋友很親切地談一點你所知道的生活”,而自己真正意義的“所知道的生活”,通常都只能是過去的生活。過去的生活也就是“回憶”。
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特點”主要是由“小說的結(jié)構(gòu)”來體現(xiàn)的。他常常是先寫環(huán)境,再寫人,而且是寫“事”重于寫“人”。其結(jié)構(gòu)是按照生活的多維流動來構(gòu)建的,也就是說,是按照生活“本來的原貌”來描寫的。汪曾祺敢于把小說當(dāng)作散文來寫,一方面是因為他學(xué)養(yǎng)豐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對自己故鄉(xiāng)的風(fēng)俗人情和掌故傳說更是如數(shù)家珍,有一種博識的雜家的風(fēng)范,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講究情趣,討厭做作,反對小說的戲劇化。
汪曾祺小說的語言風(fēng)格是由他獨特的語氣、語調(diào)和語感共同形成的。其總的特點是簡潔自然、不重修飾。《受戒》按作家自己的說法,是“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作品的開頭,一上來就是兩段夢幻式的“囈語”,簡短得不能再簡短了:“明海出家已經(jīng)四年了。”“他是十三歲來的。”開頭的簡短,意在強調(diào)語言的自然直白,用一種平靜質(zhì)樸的“語氣”給整個小說定下一個基調(diào)(語調(diào)):故事雖與夢幻有關(guān),與愛情有關(guān),但文字卻不華麗,不失自然樸素之美。正如作家自己所說,“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yǎng)。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的句子,而在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guān)系。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guān)。好的語言正當(dāng)如此。”也就是說,他不講求一字一詞的推敲的奇特,而追求整體的氛圍和韻味。
4.通過《受戒》在新時期文學(xué)史上的影響和它在中國20世紀(jì)小說散文化傳統(tǒng)中的地位,說明汪曾祺小說對當(dāng)代小說文體的意義。
《受戒》剛發(fā)表時,受到許多贊揚,也曾引起一些議論,因為它的寫法與當(dāng)時人們已經(jīng)習(xí)慣了的小說寫法很不一樣。
首先,它不但沒有一個集中的故事情節(jié),而且很不像一篇真正的小說,更像一篇散文。小說的開頭剛一提到出家的明海,馬上就筆鋒一轉(zhuǎn),大談當(dāng)?shù)嘏c和尚有關(guān)的風(fēng)俗,后來,干脆講起了小明海與小英子的愛情,至于作品標(biāo)題所說的“受戒”,直到小說的最后才出現(xiàn),而且還是通過小英子的視角來寫的。
其次,作家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也值得懷疑,總讓人想起當(dāng)時還處于文化邊緣的沈從文的小說,或者說,完全受沈從文的《邊城》的影響,不是在描寫現(xiàn)實,而是在抒寫理想。而這個理想,竟然是庵不像庵,寺不像寺,既無清規(guī),也無戒律,當(dāng)和尚的可以殺豬吃肉,可以娶妻找情人,可以唱“妞兒生得漂漂的,兩個奶子翹翹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點跳跳的……”這樣粗俗的鄉(xiāng)曲。然而,人們也發(fā)現(xiàn),汪曾祺筆下的明海聰明善良,小英子美麗多情,兩個天真純樸的少年并沒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們的童心充滿詩意,充滿夢幻色彩,成為了作家理想化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的象征。進(jìn)而人們又發(fā)現(xiàn),這種以“超功利的率性自
然的思想”,追求“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正是民間藝術(shù)中彌漫著的自然神韻,正是傳統(tǒng)文人苦苦追求的美學(xué)理想。而這一理想自“京派文學(xué)”沒落后,已經(jīng)不見蹤跡。
于是,在汪曾祺之后,隨著“尋根文學(xué)”和“先鋒文學(xué)”的興起,在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中尋找和反思,對小說文體進(jìn)行大膽地革新,以及突出小說本身的文學(xué)特質(zhì)等,都成為了一股潮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說,汪曾祺的小說連接了被中斷的“抒情小說傳統(tǒng)”,并給后來的寫作者以深遠(yuǎn)的影響。
5.汪曾祺小說在中國文學(xué)的整體格局中的個性特征。
汪曾祺小說在中國文學(xué)的整體格局中的個性特征,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小說的發(fā)展總體上都是不斷地從短篇發(fā)展到長篇,即使主要以短篇創(chuàng)作聞名的作家,也很少像汪曾祺那樣有意識地要專門在短篇小說這一文體形式上有所創(chuàng)造;二是小說的創(chuàng)作總體上都是不斷地強調(diào)內(nèi)容的社會性和人物的典型性,基本上走的是一條“戲劇化小說”的路子,即使是在小說的“詩化”和“散文化”方面有過精彩表演的作家,也很少像汪曾祺那樣能堅持始終的。
從小說體裁上看,在中國文學(xué)的整體格局中,小說是后起之秀。雖然,在先秦的《山海經(jīng)》等古籍中有《夸父追日》、《精衛(wèi)填海》等具有較完整的故事和一定人物形象的篇章,被研究者看作是“中國古小說的起源”,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創(chuàng)作,應(yīng)該是在魏晉時期,如干寶的《搜神記》等“志怪小說”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而標(biāo)志中國小說成熟的作品則是在“唐傳奇”出現(xiàn)之后。當(dāng)然,由于唐傳奇在唐代文學(xué)中的地位是無法與詩歌相比,這一文學(xué)形式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即使是在宋元以后,宋元話本的出現(xiàn)對小說的創(chuàng)作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宋元話本與我們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小說”也還存在著較大的距離。
從“小說文體”的意義上說,只有明清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才使小說本身成為了中國文學(xué)整體格局中不可忽視的一種體裁。但是,那個時代的小說家對小說文體的選擇仍然是被動的,仍然受制于作品的表現(xiàn)內(nèi)容。雖然在這兩個朝代,無論是短篇的“三言”、“二拍”和《聊齋志異》,還是長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小說藝術(shù)都真正地走向了成熟,同時也確立了自己在中國文學(xué)中地位,但是,它也很快地形成了一種僵死的創(chuàng)作模式,成為后人難以逾越的大山。
中國文學(xué)進(jìn)入現(xiàn)代以后,小說創(chuàng)作在繼承古代小說傳統(tǒng)的同時,更多地是借外國小說在形式上的靈活多變,來打破傳統(tǒng)“章回小說”的陳舊模式,小說家們的“文體意識”開始萌生。但是,由于最初多是短篇小說,直到20世紀(jì)30年代以后,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才出現(xiàn)繁榮。因此,當(dāng)時人們對于小說的文體并沒有選擇的自由和自覺。雖然魯迅的小說多是短篇,(因為當(dāng)時沒有“中篇小說”的說法,像《阿Q正傳》這樣的篇幅也是作為短篇小說看待的),但并不是他有意識地想只寫短篇,他也曾有過寫作長篇的計劃,只是因為其他原因未能完成。
進(jìn)入當(dāng)代之后,在20世紀(jì)50年代,曾出現(xiàn)過一批以寫作短篇小說而著稱的作家,在理論界也曾專門就“短篇小說”這一形式進(jìn)行過討論,提倡人們重視短篇小說的藝術(shù)價值。但是,除了有人真正看到了短篇的藝術(shù)魅力等因素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因為人們都看好長篇小說而出現(xiàn)了忽視短篇小說的傾向;二是當(dāng)時的許多作家文化水平都不高,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也不足,相對而言,比較適合于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20世紀(jì)70年代以后,短篇小說也一度十分紅火,但很快就被新出現(xiàn)的“中篇小說熱”所湮沒,再到了20世紀(jì)90年代以后,隨著稿費制特別是版稅的恢復(fù),以及出版社被拋出計劃經(jīng)濟體制,投身到商海之中,不得不以自己的生存為第一原則之后,短篇小說基本上被作家特別是有頭有臉的作家打入了冷宮,想得到她的時候不多,把她奉為座上賓的更少。
因此,像汪曾祺這樣完全有能力駕馭長篇小說,而不肯跟隨潮流,非得在一棵樹上吊死,非得與短篇小說“白頭偕老”的小說家,的確有點“特立獨行”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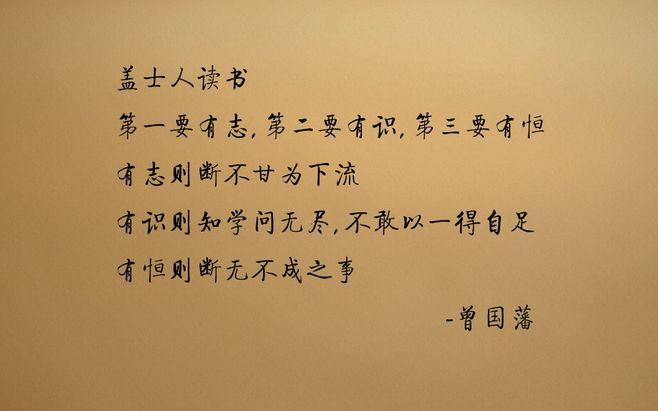
本文發(fā)布于:2024-02-06 22:37:43,感謝您對本站的認(rèn)可!
本文鏈接:http://m.newhan.cn/zhishi/a/1707230263136747.html
版權(quán)聲明:本站內(nèi)容均來自互聯(lián)網(wǎng),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yè)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quán)益請與我們聯(lián)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nèi)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關(guān)于汪曾祺的生平.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關(guān)于汪曾祺的生平.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