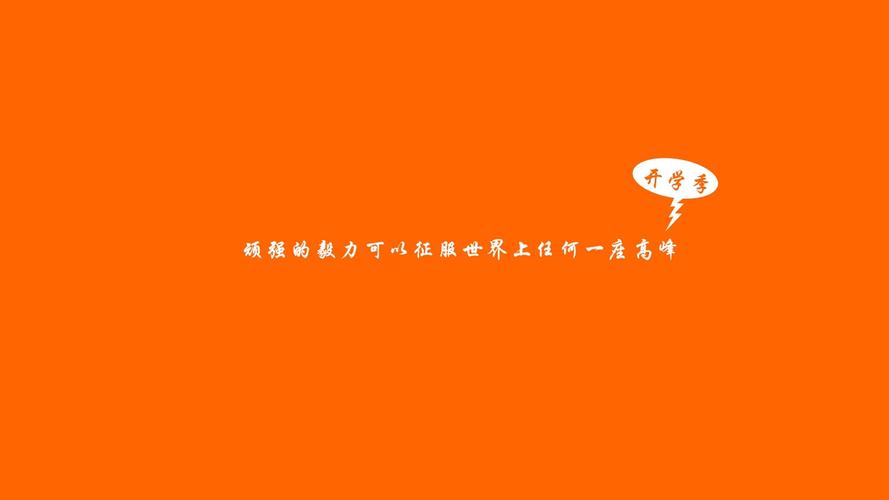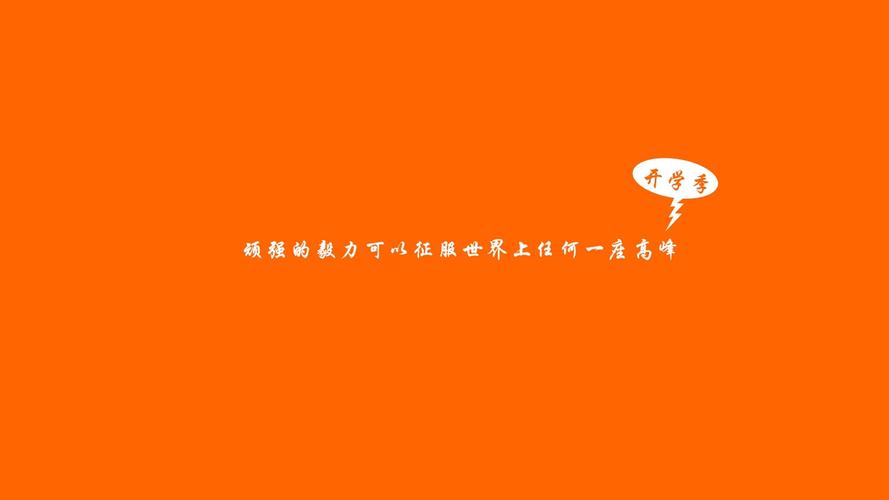
陸王學述
徐梵澄 著
非禪之悟
“狂禪解經”,是指以禪宗之說,解釋孔門之經,自明末以后,大為世所詬病。真以佛理而解釋儒經,史上大有人在,但不入所謂“狂禪”之列,儒釋兩家皆罕以為然。1 而有求會通儒釋或三教合一者,又很少不失敗。姑從“禪”學稍理出一明確概念。
佛入中國以前,當然無所謂禪宗。“禪”字本義是“祭天”,如說“封泰山,禪梁父”。祭時掃地為壇即■,因祭天之為神,所以從“示”,而變‘■’為“禪”。為壇祭天,為■祭地。假借為傳授之“傳”,為替嬗之“嬗”。佛入中國以后,以此字翻Dhyana之音,即“禪那”而簡稱曰“禪”,原義為“靜慮”,“止觀”,表一種心理上的修習。若專以“靜慮”而論,則難于說在佛入中國后始有。通常這種修習是靜坐,而靜坐是自生民以來已有,甚且很難說始于道家或神仙家。《莊子》中言及“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2 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這里所說的“無為”,意思只當于靜坐或入定。在空曠地方的大樹下靜坐,正是一常
俗事。若靜坐后作止觀或作妄想,入定或出神,皆是些不同的事。在翻譯佛典名相尚未標準化之時,“無為”亦以譯后來音翻之“涅 ”。那么,無論在后來之大乘禪、小乘禪、如來禪之類,皆可謂是佛教中的一種修為,即靜慮。而靜慮這修為,自古有之,在佛教以外各教皆有之,被稱為外道禪。即如今之默作禱告,也可歸之于靜慮。全世界各教中皆有之。道家有之,儒家亦有之,則不能說為佛教所專有。
嚴格從佛教中之禪法言之,則臺宗之九種大禪,條分縷析,頗為詳盡了。通常則此所謂禪,是如來禪與祖師禪并論。這在中國為然。中國佛教里的禪宗,是佛教入中國后一種中國文化產品,已超出印度的佛教而外。靈山即靈鷲山,其地其名至今仍在,但所謂拈花微笑而成其教外別傳者,在梵文典籍中如至今所發現者,了無蹤跡可尋。也許曾有歷史紀錄,早已隨那爛陀寺之焚毀而一并消亡;也許根本未曾有何紀錄。說為原本不立文字,只靠以心傳心。相傳中土以菩提達摩為初祖,史上菩提達摩實有其人,因與梁武論法不契,遂渡江而往北朝,入嵩山面壁靜坐九年。“一葦渡江”通常誤解為一種神異,一人立在一根蘆葦上而渡過長江。古代之“葦”,可想象為以蘆葦為蓋的木船,如《詩經》中所說“誰謂河廣,一葦航之”,河或是指黃河,而“一葦”不是指一莖蘆葦草。似乎菩提達摩所傳授者,不僅是后來的不立文字之所謂心傳,因為他最后仍是傳授《楞伽經》。其遷化“洛濱”,則是
終于華北。其“只履西歸”,有人在雪山路上遇到他手提只履,也似是神化其人的神話。而菩提達摩的師承世系,除在華文有記載外,在印度亦復無考。我們不妨假定,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禪法或靜慮之方一定同時并傳。因為最早也有《安般守意經》《禪行法想經》(均為后漢安世高譯)之類,后下還譯有《禪要秘密治病經》(劉宋沮渠京聲譯)等。到齊梁時乃發展為一獨立之禪宗而為祖師禪。3
如何從佛教本身產出了這么幾乎與之以否定的宗派呢?從歷史觀點說,這是因為佛教本身已發展到出乎凡人力所可操持的限度以外了。三藏之文字,除所譯的經典以外,即華方的著作如注疏等,已經是汗牛充棟,有如儒家之載籍既博,“屢世不能竟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既非人力可勝,自然不免棄斥。而質量上又很少新說,不足以應人心求變易求進步之需。于是在印度自龍樹而后,抵抗不過傳統婆羅門教的勢力,佛教大乘本身變質,專門轉到密乘方面去了。在中國一方面到相當限度接受了密乘,一方面來了一大廓清運動,發展了禪 宗。其次因為一種形而上的要求(即叔本華所說的Metaphysisches Bedurfnis)在凡人皆有,不限于知識分子。大致投入僧伽的,也是魚龍混雜,許多人并不識字,知識水平不高。比方禪宗六祖慧能,便是識字不多的人。由是不能以佛學之學為重,而逕直趨于學佛之佛。另外從哲理方面看:遙遙一涅 的目標在遠,一大部空宗般若的議論在前,一切如
夢、幻、泡、影,如露、如電。那么,便是一切皆空了。而究竟仍有夢、幻、泡、影、露、電,又難說為一切皆無。于是不得不說遠離二邊,契會中道。譬如說已知實是無花無相,又不可說無花無相,這是已陷矛盾,達到推理之窮,只合有無雙超,超出語言文字之外。只合默然契會,有如三方程之外,另添了一方程或二方程。衍變出無理之理,成了禪宗。
說教或教示是可以多方面的,不必專在語言名相上。日常生活,隨時隨處是教示之機,所謂青青翠竹,郁郁黃花,皆是。如莊子所云,則“每下愈況”。略看一些禪宗的大師之證道或印可之機緣,便知道是些學人將自己的全部生活皆安立其中了,而毫無所任籍。所以程子嘗說禪師是天下最忙的人。而其機鋒逞之亦不可盡。由是其三藏十二部經,可譬之爛草鞋;一棒打殺佛,也算是供養恭敬了。——這便到了儒林所指之“狂禪”,早已不限于“靜慮”一事。
一切推翻,獨辟天地,實在求真,如癡如狂,于此不以學問為長,所期只在徹悟。根本無可究詰,它早已鷂子去新羅,超乎語言而上。開口便錯,擬議即非。……諸如此類,所謂禪悟者,實與儒修相去甚遠。王學末流,或許有人也淪入狂禪,則已是不能算門墻中人了。如良種嘉植,經若干代以后,可變到愈優良,或變到薄劣。不足論。
禪家有許多公案,語錄,宋學家也有些軼事,記聞。清人有攻宋、明道學家之語錄者,古文家且以語錄為俗物,以其言羼入文章為病。“以為異端記其師語,謂之語錄,猶之可也。吾儒何必摹仿之,亦成語錄?”——這,似乎不能責備道學家怎樣鄙陋。大抵歷史文字之用不外兩匯:一記事,一記言。古史中言與事俱記,而一部《論語》,便可謂為最古之語錄。子游子夏之徒,在哲人既萎之后,收集同門多年的筆記,互相考訂,加以編纂而成,開端便是“子曰”,與語錄中開端多作“先生曰”,一般無二。或亦算子曰,則是尊稱其師為子而非孔子。可見清人之攻擊,乃是忘記了其起源,在這一點上,不是道學家摹仿了釋氏,而是禪師家摹仿了儒宗。若果有意摹仿異端,則開端宜曰:“如是我聞”,或“聞如是”。在禪宗之語錄已不如此,其出自儒門,似無可疑。是佛教語錄盛行之后,乃生此誤解。
黃宗羲議衡麓一派宋學曾涉及這問題,有云:“湖南一派,如致堂(胡寅)之辟佛,可謂至矣。而同學多入于禪,何也?”朱子嘗舉一僧語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被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愚獨以為不然。佛氏原初本是淺薄,今觀其所謂如來禪者,可識己。其后吾儒門中人逃至于彼,則以儒門意思說話添入其中。稍見有敗闕處,隨后有儒門中人為之修補增添。次第添來添去,添得濃了,以至不可窮詰。而俗儒真以為其所自得,則儒淡矣,可嘆也。”——朱子此喻只就外表形容了一大概,其實兩
家之精要,或說最深的真理,無同喻,不容增減。如來禪大大弘揚了禪宗,而得力于語言文字或竟可說文學詩詞之助,也是歷史事實。給在儒門中增添了裝飾。
自來學林有此見解,謂宋學之形成是受了禪宗的影響。這是事實。同時宋學影響了禪宗,也是事實。相互的影響,不足以證明何者為高明,較勝,光榮。程、朱皆是用心研究釋氏以及老、莊有年,然后卓立其理學,各成其教(非宗教);而禪門之南能北秀,燈印相承,自成其系統秩然。究竟禪宗是中國本土文化的產物,也無可諱言。菊花的本種不過是野地里星黃的小花,及經培植了若干代已變成如云如霞的大花了,可以為喻。又如文化交流,有時必不能不相互影響,雖欲拒斥之亦難奏效,康昆侖彈琵琶已染胡風,倘若恢復雅正之聲,必須凈盡廢棄所學十年,重新學起。思想之流傳,倘其中涵真理,真是速于置郵而傳命。往往正知覺在排斥它,而潛知覺在吸收它。究之理學之往往被誤會為禪宗者,是其教學的方式,往往相同,除了理學家不持杖打人,很少大聲斥喝或呵罵;豎拂子則非釋徒所專,早在六朝已有,難說是從西域傳來,要之指點方式,不甚相異,皆屬外表,而其教義各自獨立;儒自儒,釋自釋,壁壘森嚴分峙,旗幟鮮明,難以團結。就其外表方式一面觀之,如舉數例。
和靖(尹 )稱東皋(馮理)見伊川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事。”伊川問之。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伊川曰:“頤亦有一奇特事。”請聞之。伊川曰:“每食必飽。”4
這是門墻最高竣且反對釋氏最力的程夫子說教之方,竟似乎禪師家之說法。——“夜間燕坐,室中有光”,陸務觀游亦曾有此經驗,陸氏是從事于道家的修為的,“宣和人飲慶元春”,也很長壽。這是視神經感覺上的變異。大致這類異相出現,表示其修為功夫已深,亦恰是歧路或邪道之開端,只合任其過去,絕對不可執著。程子了不以此為奇,可謂大具手眼。而這一問答,從外表看,不異于一禪門公案。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眾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值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后知。”堯夫曰:“子以為起于何處?”子曰:“起于起處。”堯夫瞿然稱善。5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時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卒。6
這幾則例子,皆屬外表,然正是后世誤解之由來。于宋儒尚指其為狂禪,于明儒之未及宋儒者更不必說。清世漢學家之非毀道學,多以這些外表現象為疵病。那在現代皆感覺其無謂了。儒釋之爭非此所論,北宋諸道學家,如謝上蔡,東萊三呂,楊龜山晚年,游 山初年,——“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里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7 ——皆是曾致力于佛學的。也可疑大程子亦復深通禪理,然二程子以及后來的朱子,皆是大力攻擊釋氏的,維護了道學的傳統。大率言之,諸儒之見道有得皆非由于釋氏,其立身、行道、說教皆不外于儒家,其特色有二:一是直由孔孟而見道有得,一是可不由師授而明理成宗。二事在某些人只是一事。換言之,即大徹大悟,而卓然獨立。若是必于佛教求葛藤,則可說諸人皆屬“獨覺”,——不必說“緣覺”,因為梵文之“獨覺”(Pratyekabuddha)一名詞,音譯“辟支佛”,或譯“缽刺翳伽佛陀”,本字無“緣”義。舊說為觀飛花落葉而成道者,即不必附會其悟十二因緣而謂之“緣覺”。以其講學而論,在釋氏則皆說為屬十地菩薩。但總歸一樣,其人是曾大徹大悟,在世俗中即所謂“上了岸的人”。
一有徹悟便稱之為釋家,這是流俗之錯誤見解。不單是由儒而悟道,由他道或其他宗教皆有證悟之事。籠統皆指為禪悟,是謬見,誤解。茲再從宋儒中錄出幾例,證明確實有這回事。象山正是由讀《孟子》而見道,無直接從而傳授之師,純由自力,獨立成宗。
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
先生(王信伯)正容曰:“萬物皆備于我。”
某于言下有省。8
林拙齋記問曰:天游嘗稱王信伯于釋氏有見處。后某因見信伯問之。信伯曰:“非是于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令看《論語》,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之良久,既于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又忽讀。忽然有個入處。因往伊川去吐露。伊川肯之。”某因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信伯曰:“當此時,面前樽俎之類,盡見從此中流出。”
按:此解釋孟子“萬物皆備于我”一句,竟無言說,而聞者有省。全祖望謂其“近乎禪家指點之語”。然這不是無意義話頭。下二句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正解是萬事皆具于心。雙泯主體客體擴大此心為萬事萬物而同此一我,正是內證之事,要有所體會,于是有省。全氏也只說這“近乎禪”,即似禪而非也。“見處似釋氏”,即在儒門有此見解,似釋而非也。讀《論語》兼靜坐忽然有悟,往告伊川(在禪家則多是呈四句偈語,經老師印可),于此則
伊川加以肯定,兩家程序又是相同。這顯然難說是從釋氏入,乃其見處似釋氏。總之,皆是外在表相。
于此有牽連象山之處。全氏云:“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為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后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啟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為遙出于上蔡。予以為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9
王蘋(即信伯)之弟子陳齊之(即陳唯室),亦福建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10 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得。’——齊之其后有詩曰:閑花亂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系停。問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方有所自得。”11 于此詩可見與上堂呈四句偈也不甚相遠。信伯之徒,亦主直指以開人心。必不可誤認為禪。此即謝山所云“程門已有此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