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4日發(作者:明媒正娶是什么意思)

上海城市空間重構過程中的記憶、地方感與“士紳化”實踐
潘天舒
【摘 要】文章以田野體驗和實地觀察為基礎,論述上海城市發展語境中普通民眾
的空間二元論對于社區重構的意義。筆者認為:將個體與集體記憶與權力結構和特
定地方和鄰里相聯系,有助于我們觀察、了解、體會和分析具有新上海特色的“士
紳化”進程對于城市社區重塑的深遠影響。筆者的初步發現表明:摧枯拉朽般的造
城運動并未減弱當地人由來已久的地方歸屬感,相反,這種地方感會隨著社會分層
的加劇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成為當代都市話語和實踐中的
有機組成部分。%Bad on ethnographic field rearch ,this paper probes
the local grounding of the ongoing place‐making process in terms of
the “lower/higher quarter” dichotomy and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s
in Shanghai’ s gentrifying neighborhoods . Making explicit links between
historical memory and place attachment ,the paper attempts to locate the
cultural symbols in actual sites so that upper quarters and lower
quarters ,as imagined communities ,come to be attached to imagined
places . Using the intimate perspectives provided by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t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locality power embedded in the
dichotomy —the ways in which it is exploited ,the memories to which it is
linked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explanations it provides for prent‐day
reconfigurations of social space and redistributions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post‐reform Shanghai .
【期刊名稱】《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年(卷),期】2015(000)006
【總頁數】8頁(P62-69)
【關鍵詞】上海城市變遷;記憶與地方感;“士紳化”進程;田野視角
【作 者】潘天舒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上海 200433
【正文語種】中 文
【中圖分類】C912.81
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上海城市的每個角落都經歷了開埠以來最大的一次改造,
其變化程度之劇烈,可謂滄海桑田。為重振昔日東亞經濟中心雄風而推出的一系列
市政建設項目,完全達到了規劃者所預期的“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效果。
過去的十多年間上海城區內工地之多以及市區交通地圖版本更新速度之快,也可以
說是舉世罕見的奇跡。在轉瞬間就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環路、南北高架橋、橫跨浦江
兩岸的斜拉橋、隧道、地鐵、輕軌和磁懸浮列車,同林立的摩天大樓一起,改變著
城市居住者原有的時間和空間概念,也呈現出上海成為新型國際大都市的前所未有
的人文和社會生態景觀。
目睹如此世紀劇變,我們也許會認為所謂的區域性和地方情結也將隨之淡化或消失。
然而,筆者在1998年至2002年以及2010年世博會期間在上海東南部灣橋社區
所進行的田野體驗和實地觀察顯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當地人在利用自己居住
地點在城市所屬區域來喻指自己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并借此抒發文化優越感或者自卑
感之時,仍會不經意地使用早該過時的“上只角”和“下只角”陳舊說法(Pan
and Liu, 2011)。筆者驚奇地發現:這種理應存入歷史語言學檔案的老掉牙的空間
二元論,居然還有相當茁壯的生命力,能繼續成為探討今日上海城區結構調整和公
共生活變遷在具體空間體現形式的一個象征符號。不久前由于閘北和靜安兩區合并
在網絡和微信引起的眾說紛紜即是明證。
與其他國際大都市的市民相仿,在上海世代生活和工作的居民都會在日常交談閑聊
時以地段或者“角”這樣的傳統說法,來特指其在城市生活的社區,并以居住地點
來暗示其社會和經濟地位。這種微妙的表達方式所透露的是社會關系與空間等級布
局之間的邏輯關系。“角”在實際使用中產生的多層含義,涵蓋了阿格紐(Agnew)
所闡述的有關“地方”概念的幾個方面:首先是指形成社會關系的場所或地點(即
所謂的locale);其次是地段(location),它是由社會經濟活動而拓展的更廣的范圍;
當然還有人們對特定地點和場所產生的“地方感”(Agnew, 1987: 28)。一百多
年來在上海方言中頗有市場的“上下只角”之說,仍然不失為居住者以空間地理位
置為自己定位的一種策略性話語手段。
本文試圖探討城市中心特定地方的集體記憶對于公共話語構建和特定地方營造的現
實意義。在上海,承載極具地方色彩的記憶在公眾話語中的表述,便是代代相傳的
“上只角”和“下只角”之說。著名人類學家阿鮑杜萊(Appadurai)曾經吁請人類
學學者在田野研究中注意“將等級關系(在特定地方)定位”的方法。作為回應,筆
者在文中將以上/下只角的說法為觀察切入點(而非分析框架),描述“上只角”和
“下只角”作為想象社區是如何被作為文化和社會標簽“貼在想象的地方之上
的”(Gupta and Ferguson, 1997:37)。
一、“上只角”/“下只角”二元論與都市空間重構
在上海方言里,“上只角”可直譯成英語里離人口繁雜地段有一定距離的幽靜的富
人住宅區(uptown);而“下只角”則是擁擠的窮人聚居區(如棚戶)的代名詞。
“上下只角”二元論,在身處歐美工業社會語境的社會學家看來,在體現階級和族
裔差異的空間和地方感方面,也不失為一種絕妙的表達方式。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多
年間,上海歷經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洗禮,成為“十里洋場”和華洋雜居的繁華都市。
這一空間二元論,卻始終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個人或家庭乃至社區鄰
里層面的生活歷程。它在話語表述中所展現的,是一種對于本土或出生地的認同感
和對于目前所處生活環境的體會。社會史學者早已敏銳地察覺到這一空間二元論所
凸顯的社會優越感和市井勢利性(Honig, 1992;Lu, 1999:15,376) 。如下
文所述,作為歷史想象力和社會現實的雙重表征,這一空間二元論不失為本地居民
(包括已經扎根立業的“新上海人”)、各級官員和房地產商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定
位參照點。尤其是在新世紀上海社會各方面發生劇變之際。
所謂的“上只角”就是指上海在鴉片戰爭后成為租界之后來自英法美等國的洋人的
住宅區。現在的衡山路、華山路和武康路地區,靜安區南部,盧灣區(現已經歸屬
黃浦區)北部,是久居上海的市民公認的典型的“上只角”(徐中振等,1996:42)。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強瓜分上海這塊寶地,以租界形式來劃定各自的勢力范圍。法
租界和公共租界(代表英美勢力)成了“上只角”的歷史雛形。不管是昔日公共租界
內的外灘和南京路十里洋場,還是法租界內幽靜的舊別墅區,如今都是方興未艾的
“上海懷舊”產業的文化地標。即便是在1949年以后,那些收歸國有的西式樓宇
也繼續在為新政權的各個相應政府部門服務,其建筑風格也得以維持保留。在“上
只角”地段,人們不時能看到在梧桐掩映之中的多數已經易主的舊宅大院,青苔掛
壁,卻風韻猶存。
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規劃的一大特征是控制人口和固定戶籍(Ma and Hanten,
1981;Whyte and Parish, 1984) 。由此上海內城的“上只角” 的地位,并沒
有因為九十年代城市改造的浪潮而下降。居住在“上只角”內的眾多寧波籍居民在
言談舉止間流露出的優越感,往往源自居住地的象征意義,而未必是實際的居住條
件。比如當某位帶有濃重寧波口音的老人說“我住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時,我
們完全可以猜測其實際的居住地點不過是在一棟年老失修的公寓樓里。但在房地產
開發尚未成氣候時,居住方位(即“上/下只角”)對于寧波移民的后代們來說遠比
居住條件重要。
對于居住環境中處于“上下只角”之間的南市老城廂來說,這種夾在地段優劣程度
與實際住房條件之間的矛盾更為突出。現已成為黃浦區(其轄區覆蓋了原公共租界
地段)一部分的南市,曾是上海市人口極為稠密的居住區。區內本地老屋和舊式石
庫門里弄鱗次櫛比,是極富上海本土特色的居住模式。近年來,旅游業的興盛使該
地區煥然一“新”的城隍廟、豫園、文廟、茶樓、老字號的飯店乃至遺存的上海縣
城城墻,成為重要的文化地標。但是,這些地標周圍的居住環境卻令地方官員難堪。
蘊藏在本地居民中的那種和無奈交織的情緒,使他們不愿遷往近郊新開發的住宅區,
而寧肯忍受合用公共廚衛以及馬桶帶來的不便、煩惱和尷尬。一方面老城廂的悠久
歷史使他們對于世代居住的街區有一種歸屬感,另一方面,由于“上只角”近在咫
尺,老城廂的居民還時而慶幸自己能在心理上保持與“下只角”的距離。
在上海鬧市區與“上只角”相對應的“下只角”,是那些擁擠不堪的棚戶區。在城
區大規模改造之前,上海的“下只角”通常包括從周家角到外白渡橋的蘇州河兩岸,
北部的滬寧鐵路和中山北路之間地區,南部的徐家匯路以南,中山南路以北地區
(徐中振等,1996:42)。“下只角”的傳統居民是來自鄰近蘇北地區的移民或難
民的后代,經常說一口帶有濃重家鄉口音的上海方言。在最能體現上海普通市民文
化生活的滑稽戲表演中,蘇北口音就是一種象征演劇中小人物處于“下只角”卑微
社會地位的符號。這種藝術的真實的確是生活現實的反映。而寧波口音由于甬籍經
濟勢力的強大而成為上海方言的一種標準音(如從“我呢上海人”到“阿拉上海人”
的變化所示)。早在20年前,加州大學教授韓起瀾(Honig)就指出:“蘇北”在語
言使用中實際上已失去指代籍貫的作用,而是一個充滿歧視色彩的詞匯(Honig,
1992:28-35)。由此在上海的社會空間中,“下只角”成了針對以蘇北人移民為
主的下層平民的偏見的源頭。與世界上多數地方對貧民居住區固有的誤解和成見相
似,上海“下只角”的棚戶區常常被認作充斥陋屋和違章建筑,破碎家庭,社會風
氣敗壞,是陷入貧困泥潭而難以自拔的“都市中的村莊。”可以說在長達半個多世
紀的時間里,“上只角”是以寧波移民群體為代表中上階層上海市民而努力追求的
一種代表現代和文明的美好理想,“下只角”只能屬于落后、愚昧和“缺乏文化教
養”的下層移民和他們的后代。
上海研究學者瓦瑟斯特穆(Wasrstrom, 2000)曾質疑中外學界將租界時期定位
成中國現代性發展重要標志的傾向,從而間接對“上下只角”二元說法在學術探究
上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戰。筆者在對他深邃的歷史眼光表示欽佩的同時,不得不指出:
作為都市生活集體和個人生活體驗的一種地方性知識,“上下只角”的二元論在地
方行政區劃實踐中確有參照系的作用,使地方官員對某一地段居民的社會背景有所
了解。1949年以后,新政府對上海城區重新進行劃分,力圖改變租界時代留下的
格局。新設立的區常常將“上只角”和“下只角”一并納入,以體現新社會所倡導
的對居住條件不同的居民區一視同仁的平等精神。在地圖上,“上只角”和“下只
角”的界限隨著地方政治版圖的改變(如靜安和閘北兩區合并)已幾乎消失。然而,
為什么在日常話語系統里,這一本該作古的二元論還有市場呢?
應該說,在1949年之后租界時代遺留的以路標、馬路和建筑區隔“上只角”和
“下只角”的做法已被擯棄。然而,在新設區內設立的街道和居委,有意無意之間
又延續了以行政手段區分“上下只角”的做法。如盧漢超所指出的,街道組織領導
為了方便日常工作和管理,索性用居民出生地的地名來命名居委會(Lu, 1999:
316) 。在上海人眼中,“蘇北里委”和“南通里委”這些實實在在的社區的社會
和經濟地位及其名稱中所蘊含的象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上只角”原法租界的霞
飛路,盡管在嶄新的政治和社會語境中被更名為淮海路,但對于居住在那里的普通
居民或是慕名而來的“老上海迷”來說,它所代表的特殊的歷史風貌、藝術品位乃
至文化資本(Bourdieu, 1984),仍然未見絲毫減少。
誠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社區》一書中所言,革命者在取得勝
利后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去承繼其前任的遺產(on, 1991:160-161),而并
非真的在物質上毀滅舊時代留下的一切東西。如原上海匯豐銀行大樓,在成為浦東
發展銀行之前,一直作為市政府行政大樓,是外灘的標志性建筑。外灘的其他風格
各異的西洋建筑,長期以來也發揮著市政府的商貿和其他部局單位的日常辦公功能。
正是由于這些足以成為上海歷史文化遺產的樓堂會所的客觀存在,使得“上只角”
的符號表征意義在新的形勢下沒有實質性的改變。相反,這一“上/下”二元論在
不同社會交往情境中,繼續成為人們在日常談吐中區別高低和貴賤的重要指標。
二、城市社區的“士紳化”進程
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基建和商業發展項目,在快速地重構著中國沿海和內地城市的社
會空間。與經濟和社會轉型同步的城市化進程,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和重塑城區的新
舊鄰里之間的互動關系。導致中國城市面貌改變的因素,并不僅僅是樓宇和道路,
還有過去十年以來規模空前的人口流動。彈指之間,昔日寧波幫的后代已成為地地
道道的老上海。在日常會話中,經過寧波方音改造的上海話比原本聽上去更接近本
地土話和吳儂軟語的上海方言要更為標準和自然。當然上海話的實際發音體系中也
在不知不覺中加入了個別蘇北方言的元素,變得越來越多元和多源。這一過程暗示
蘇北移民的后代在隨著下只角被推土機碾為平地之后,告別了不堪回首的個人和社
區的過去。而他們在城市社會生活中飽受不公待遇的地位已被如潮水般涌入的民工
群體迅速代替。
隨著改革的深化,主導城市管理層的是新一代具有專業知識和國際眼光的政府官員。
與老一代相比,他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新穎的思路和強烈的進取意愿,來應對新
的歷史條件下城市擴張和“流動人口”劇增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城市產業結構
調整和國企重組過程中采取的一系列包括消腫和分流在內的措施,使得數量可觀的
待崗和下崗職工,逐漸代替老弱病殘,成為社區“困難人群”的主要組成部分。盡
管上海有領先全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應付下崗帶來的社會問題仍然是城市管理的當
務之急。由于上海在20世紀一直是國家重輕工業集中的超大型城市,紡織等產業
在結構調整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許多傳統的制造行業都有不同程度的下崗
現象存在。必須指出的是,市內未開發的“下只角,”是“吃低保”(享受社會福
利待遇)的下崗工人和其他困難人群的主要集中地。許多待崗和下崗職工,在一夜
間發現,他們得努力去適應一種以他們居住的社區,而不是以單位為軸心的所謂
“社會人”的生活方式,不管他們對此有無思想準備。
跨國公司和私有企業的涌現,也使城市的社會和經濟生活變得更加多元。全球化浪
潮所帶來的各種知識、技術和觀念的普及,也在漸漸地影響上海都市“上下只角”
的社區改造思路。社區管理和社區服務的專業化和細分化,以及強調社區有序發展
和注重經濟效益的路徑選擇,正在主導著城市舊區改造中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高檔
化和“士紳化”進程(gentrification)。作為后工業化社會所特有的城市社區重構
和住宅建設變化模式,“士紳化”(高檔化)這一社會學家所造的詞匯所描述的是最
近二三十年歐美大城市(如倫敦、紐約和華盛頓等)的一種復興和重塑過程
(on, 1990; Butler, 2003;Caulifield, 1994)。依照城市社會學的一般
共識,“士紳化”的典型表現形式為:高收入的專業人士遷入改建后住房條件和治
安狀況顯著改善的內城,同時社區重建所引起的房價和租金上漲,使久居內城的低
收入居民(以少數族裔和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為主)被迫外遷。房地產開發商、當地
政府官員和新近遷入的高收入人士都在“士紳化”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近幾年來因商務和學術研究久居上海的歐美人士,在談到上海市中心及周邊地帶在
近十年發生的矚目變化時,都會使用“士紳化”這一詞匯。但要更好地理解這一具
有當代中國特色的“士紳化”進程,我們不能脫離住房改革、地方行政管理的專業
化和基建發展的大背景。在20世紀末上海城市改造的具體語境中,“士紳化”首
先表現為一系列旨在美化市容和改變文化景觀的市政措施和建設項目。與歐美和許
多發展中國家城市發展所經歷過的富裕人士因窮人不斷遷入,“放棄”內城,在近
郊購置房產所不同的是,在上海,即便是擁擠的內城和鬧市區也有相當部分屬于
“上只角。”而來自海內外各種社會和經濟力量近年來對這部分“上只角”所展開
的空間重構,是值得城市研究者認真關注的“士紳化”進程的重要方面。總之,
“士紳化”作為一股造就上海文化生態景觀的結構性力量,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制度、
決策和規劃機構,也是自下而上的植根于鄰里社區的組織和網絡。
“士紳化”進程的催化劑是以懷舊為主題的老上海文化產業。以上海懷舊為題材的
小說、戲劇、影視劇、攝影集、回憶錄、散文、音樂和物品收藏等一系列文化產品
的創作、營銷和消費,就其內容和形式而言,無非是對當年十里洋場繁華舊夢的回
味、想象和詠嘆。這一懷舊產業的興盛,得益于上海在城市改革進程中涌現出的來
自海內外社會精英人士的精心策劃和推介。當然,上海懷舊的產業化也為研究觀察
都市文化變遷與城市規劃和社區構建之間的互動提供了寶貴契機。透過懷舊的表象,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饒有意味的對老上海集體記憶的重新發掘、重新評價和再度包裝
以期重現和重構文化的復雜過程。基于筆者的觀察,對于記憶的策略選擇和歷史的
想象重構,是人們在經歷城市百年未有的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巨變時的回應。從某
種程度上講,上海懷舊能使城市的新生代精英(如各級政府官員,作家和藝術家,
建筑師,房地產開發商和白領人士等)回味大都市的昔日輝煌,“以史為鑒,”為
實現規劃藍圖,營造新世紀的全球化都市做好熱身準備。從新天地到思南公館以及
徐匯和靜安的學區房,都是特定地段和社區“士紳化”程度在嶄新語境中的鮮明體
現。
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在筆者的主要田野點灣橋社區以北的“上只角”地段,
各類租界時期的公寓樓、別墅和洋房修繕一新,與時下興建的風格迥異的高層住宅
和辦公樓相映成趣。的確,日漸多元化的建筑與景觀設計,在盧灣北部商業中心周
邊高檔消費區(以新天地為代表)刻意凸顯的新“上只角”氛圍,與美國波士頓城舊
區改造“士紳化”杰作之一的昆西市場旅游景點,可謂異曲同工。公共藝術和燈飾
的巧妙使用,使一些歷史建筑舊貌換新顏。同時,一些廢棄的老廠房和車間經翻修
重整,成為時尚設計室、畫廊和工作坊。位于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處的新天地
多功能消費和娛樂區,與紅色圣地“一大”會址比鄰而居,集歷史凝重、現實思考
和未來憧憬于一體。在這里,投資者煞費苦心,耗資千萬,打造以展示上海石庫門
民居風格的新舊混合建筑群體,其轟動效應非同一般,引得遠近游人紛至沓來。新
天地在商業上的初步成功,使市內其他地段(尤其是位于“上只角”附近住房條件
陳舊的一些街區)紛紛效仿,以重建文化街和維護滬上舊別墅群為目標,試圖再造
“新天地,”從而人為地加快和加深新時期海派“士紳化”的程度。
從理念上講,在城市改革語境中依靠市場和文化重建的力量來促進街區“士紳化,”
比單純依賴行政手段來進行美化市容和塑造文明社區要更為有效和持久。然而,與
后工業化城市復興實踐經歷相仿的是,真正受益于“士紳化”的往往是經濟轉型時
期的寵兒,而低收入人群卻難以欣賞和分享良好的家居環境和治安狀況帶來的好處。
20世紀90年代末,南部灣橋的“士紳化”進程與其北部“上只角”地區要緩慢
得多,筆者在街道結識的那些干部朋友們為此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以灣橋所
在城區的街道設置為例,我們不難看到這“上/下”二分論在考察“士紳化”過程
中的實際意義。該區北部的三個街道大致位于“上只角”內,而位于南部的灣橋則
是聞名遐邇的“下只角,”由一個街道單獨管轄的小型行政單元。與市內其他的
“下只角”相類似的是,灣橋街道的老居民多是解放前逃荒和躲避戰亂的難民和本
地菜農的后代。在1998年初次進行人類學田野研究時,筆者不無驚訝地注意到:
那已經變了調的蘇北和山東方言,在某些里弄,是比上海話更為有效和實用的溝通
語言(Pan, 2007,2011)。如下文所述,灣橋在地段、居民出生籍貫和當地人口的
社會成分方面,的確具備“下只角” 的一些污名化特征。
筆者發現:不管是上海本地人也好,或是研究上海的專業學者也好,對于“上/下
只角”這一二元論,有時會有一種不屑一顧或莫衷一是的態度。這種難以啟齒的感
覺,類似于我與來自印度的學者談到種姓和美國同學論及族裔和階級差異話題遭遇
的莫名的尷尬。一般來說,相對于其他階層,具有婆羅門背景的印度同學更愿意帶
有一種優越感來談論種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而低種姓階層的人士則會高談闊論
圣雄甘地廢除種姓差異的壯舉,而閉口不談平等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在筆者曾
任教的美國喬治城學院,來自中上層背景的美國白人學生會輕松地談論起他們所居
住的高尚住宅區以及同樣高尚的鄰近學區。而來自華府東南黑人區的學生則干脆以
“巧克力城”(喻指其所屬種族的膚色)作為首都的昵稱,在心理空間上與居住在華
府西北部的精英人士保持距離。
筆者的童年是在黃浦區的一個住房類型混雜、與盧灣區北部一街之隔的社區(位于
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處)度過的。然而多年來筆者從不記得街坊鄰里由誰提起
過在本市東南部有一個叫灣橋的地方。當筆者在與街道和居委會的朋友們談起自己
竟然對灣橋這一近在咫尺、比鄰而居的實實在在的社區如此無知而感到羞愧時,他
們卻十分大度地告訴本人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用他們的話來說,灣橋不過是
“盧灣的下只角而已。”言下之意,沒有人會在乎下只角的存在,尤其灣橋這個下
只角還有“盧灣的西伯利亞”這一具有侮辱性的別號。
在田野研究過程中,筆者逐漸感覺到,灣橋的“下只角”地位,因為一些附加的歷
史因素而變得更加獨特。首先,1949年前興盛的當地殯葬業,是數代居民堅信的
敗壞本地風水的重要根源。1937年日軍空襲上海之后,成千上萬的無主尸體未經
喪葬儀式,便掩埋在灣橋,填平了眾多臭水溝,也進一步污染了當地的文化生態環
境。在解放戰爭期間,灣橋的某些傳說中的“鬼魂”出沒之地,成了國民黨殘兵、
流寇和因土地改革而逃亡來此的地主的歇息場所。這段當地老居民覺得難以啟齒并
希冀塵封忘卻的歷史,卻又在九十年代大興土木的基建和住房改造高潮中,破土而
出,顯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有些建造摩天辦公樓和高層住宅的工地,挖土機掘地
數尺之后,工人們便會驚恐地看到遺骸和尸骨。這些不經意的發現,又會勾起老一
代的記憶。難以考證的瑣碎敘述,經過街坊內外的道聽途說和添油加醋,變成一種
“歷史事實,”成為工地附近的居民寢食不香的緣由。
1949年前的灣橋,亂草叢中,死水潭旁,處處蚊蠅滋生。據老居民回憶,夜出無
街燈,受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打劫乃是家常便飯。白天外出常會看到棄嬰和饑寒交
迫,流落街頭的乞丐,甚至還有破草席包裹的凍死骨。一位已退休多年的街道干部
告訴筆者:灣橋在1950年之前本是一片藏垢納污之地,連一所學校也沒有。與北
部“上只角”的居民區相比,灣橋無疑是被歷史遺忘之地,其居民不幸成了是“沒
有歷史的人們”(Wolf, 1982) 。在區政府派往灣橋工作的干部眼中,灣橋與該區
北部的反差巨大,缺乏文化、歷史和傳統,簡直就是他們的“傷心島。”
有意思的是,就地理位置而言,灣橋與市內地處邊緣的“下只角”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是灣橋距其北部“上只角”街區的步行時間不過十來分鐘。也就是說,灣橋離
眾多歷史地標,尤其是那些象征“標志式時間”(Herzfeld, 1991)的建筑,僅一箭
之遙。灣橋之北是中共一大會址和在此附近興建不久的“新天地”高檔娛樂區。灣
橋之南則是被稱作中國工人階級搖籃的江南造船廠(原江南制造局)。灣橋之東是豫
園城隍廟旅游景區。由灣橋向西行二十分鐘,便是遠近聞名的徐家匯地區。在灣橋
北部的“上只角,”在上海懷舊文化產業和政府歷史建筑保護措施驅動之下,租界
時代風格各異的建筑修葺一新。出于不同的商業目的,老洋房、老公寓樓和里弄石
庫門等等,或整舊如新,或整新如舊。建筑文化的再次發明似乎在暗示慕名而來的
參觀者該區法租界的昔日風采。
直到20世紀末,你如果從盧灣北部向南往灣橋方向走去,不難發現你視線中房屋
建筑風格會“移步換景,”從夾在后現代風格摩天大樓之間的歐式洋樓,到傳統的
石庫門排樓以及式樣統一的新村樓房。到了灣橋,你會看到老工房,低矮的本地老
房,和尚未拆遷的棚戶內為拓展生活空間“違章搭建”的小屋。在鱗次櫛比的高樓
還處在城建規劃館的模型展示盤的發展階段,你在灣橋所看到的是新舊交替的真實
生活圖景。
在1995年成為文明社區之前,灣橋從未被外界重視。在厚達200多頁的區志中,
占地三平方公里、擁有八十多萬常住戶口居民的灣橋,只有區區兩三頁的介紹。在
眼界甚高的地方官員眼中,本區的亮點從來就應該是其北部文化氣息濃厚的“上只
角”,而絕不是相形見絀的灣橋。難怪在2000年夏天當筆者將剛完成的一份涉及
灣橋1949年前歷史的田野報告面呈一位街道干部時,他頗不以為然地說道:過去
的事情有什么好研究的,而且這么小一塊地方也值得大書特書嗎?顯然新一代的街
道和局委干部,似乎沒有那種懷舊情緒,他們的著眼點是社區的現狀和未來,而灣
橋作為“下只角”的過去,只是一個可以甩去的歷史包袱而已(Pan, 2007)。
雖然居委會和街道干部朋友們對灣橋的過去興趣寡然,但我對于灣橋地方性知識的
進一步探求,也許冒犯了那種人類學家所說的充溢著“文化親密度”的集體空間
(Herzfeld, 1997)。筆者在隨后的幾次訪問中得知,有關灣橋過去的訊息(尤其是有
關風水的說法),如果被好事者大肆渲染,會間接地損害到地方發展的經濟利益。
比如,位于大路兩側的硬件和設施相似的新建住宅區,由于一個接近“下只角,”
另一個則屬于原租界的南側,兩者間每平方米的房價可相差近1000元人民幣。其
中來自港澳臺的風水先生通過調查(主要是對灣橋過去的探尋)得出的結論,對房價
的高低起了市場之外的“調節”作用。與城內其他原“下只角”地段的街道和居委
會干部一樣,灣橋的地方官們竭盡全力,通過積極參與文明社區和其他社區發展活
動吸引傳媒的注意力,以改變人們對社區的刻板印象。從20世紀50年代到本世
紀初,每一屆街道領導都以擺脫灣橋的落后面貌而傾注無數汗水和時間,試圖在這
白紙一張的“下只角”中描繪出美妙的圖畫。他們意識到,存在于灣橋歷史記憶的
潛在力量并未隨著時間而消逝。而他們的努力方向,恰恰是要使這種集體記憶轉化
成社區“士紳化”的驅動力。
對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使上海走向從制造業逐漸發展成以服務和金融業的面向
高科技未來的國際大都市的軌道。這一城市產業的結構性調整,在不同程度上影響
著盧灣北部(“上只角”)和南部(“下只角”)的“士紳化”過程。在北部,保存完
好的租界時期的洋房和傲然屹立的摩天樓宇,似乎預示著新一代城市的主人在努力
恢復昔日東方巴黎和亞洲商業中心地位的決心。在這里上班的白領們充滿自信和活
力,體驗著其父輩所夢想不到的職業人生。而與此同時,南部的灣橋卻在目睹國有
企業重組關閉,職工分流和下崗的尷尬場景。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展現在盧灣的
這種反差極大的南北生活方式,似乎又拉大了上下角之間的距離。
房地產開發商在廠房拆除后的土地上,建造起了高級住宅小區。在新生代街道領導
的眼里,遷入這些小區的居民大都有相當高的教育程度和專業背景,能極大地提高
街道的人口素質,是灣橋保持其文明社區光榮稱號的重要保證。于是,灣橋的新建
小區,開始代替傳統的工人新村,成為街道社區發展項目試點和推廣的主要對象。
盡管遷入高檔小區的居民對灣橋社區毫無感覺,他們卻成為街道干部在參加市級文
明社區評比中的取勝關鍵。由于新建小區的“軟硬件”設施較灣橋的普通新村更為
完善,街道將其視作向外界展示其促進社區發展和推動基層民主的示范點。結果,
還未完全認同灣橋社區的新居民,卻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居委會選舉和業委會組建的
生力軍,在媒體中曝光率極高。而在多數傳統新村中的老居民卻在社區日漸“士紳
化”之際,成為可有可無的陪襯“邊緣人。”而正在城區之內蓬勃興起的“上海懷
舊”產業,就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在城市生活中的服務對象而言,還是以重現“上
只角”當年風貌,迎合當今時尚潮流為主要特色。對于同屬一區但地處灣橋“下只
角”的平民百姓來說,其意義實在有限。
令筆者寬慰的是,灣橋的世博文明社區建設經驗似乎又再次印證了地方歸屬感和集
體共享記憶的珍貴價值。日新月異的時空變幻圖景,通常會使管理者忽視社區鄰里
內部原有的人情和倫理資源對城市凝聚力、城市治理的公共文化意義和實際價值,
而無形的社區內道德傳統力量一旦流失,則需要有形的公共資源來彌補,被割裂的
社區網絡也平添了公共的治理成本。灣橋與2010年上海世博會園區僅一箭之遙。
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在世博舉辦期間所占據的展示社區文明舞臺的重要性。
在增強鄰里功能、追求管理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新一代的街道干部在實踐中嘗試
降低日常行政運營的間接成本,同時積極迎應士紳化的趨勢,適時營造對社區成員
產生影響的公共文化氛圍。而這種公共文化的氛圍是以自發的和受到激勵油然而生
的志愿精神為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的。社區內原有的各種關系網絡、成員之間的信任
感和責任感以及對行為規范和道德倫理的認同和行動上的默契,也為志愿精神的培
育和發揚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充沛的能量。熟悉的鄉音、對于小區里弄新村內一草
一木的共同記憶以及源自孩童時代的同窗友情,也會使志愿精神得以延續和拓展。
本文從滬人皆知的“上下角”空間二元論入手,論述特定社會語境中歷史記憶對
“上下只角”這些想象社區的空間重構的作用。城市人類學者所強調的將個人與集
體記憶與權力結構和特定地方相連的研究手段,有助于我們觀察、了解、體會和分
析具有新上海特色的“士紳化”進程及其城市中心社區發展的推動和限制作用。有
鑒于此,筆者認為:摧枯拉朽般的造城運動,實際并未造成人們地方感的消失,相
反,這種地方感隨著社會分層的加劇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
成為城市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參 考 文 獻
【相關文獻】
[1] Agnew,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M].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7.
[2] Anderson, 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M].Revid : Verso, 1991.
[3] Anderson, wi: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4] Appadurai, A .Putting Hierarchy in Its Place [J].Cultural Anthropology, 3(1988): 36-49.
[5] Bourdieu, 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ment of Taste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Butler, Calling: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Inner London
[M].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3.
[7] Caulfield, Form and Everyday Life: Toronto’s Gentrifica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8] Gupta, Ferguson, 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M].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Herzfeld, M.A Place in History: 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 Herzfeld, 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11] Honig, ng Chin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 Lu,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3] Ma, Hante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M].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1.
[14] Pan, orhood Shanghai [M].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7.
[15] Pan,Tianshu and Zhijun Matters: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Historical
Memory, Place Attachment, and Neighborhood Gentrification in Post-reform
Shanghai[J].Chin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43.4(2011): 52-73.
[16] Wasrstrom, oning the Modernity of the Model Settlement:Citizenship
and Exclusion in Old Shanghai[M].n and ed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M].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0-132.
[17] Whyte,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8] Wolf,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19] 徐中振, 盧漢龍,馬伊里.社區發展與現代文明:上海城市社區發展研究報告[M].上海:上海遠東
出版社,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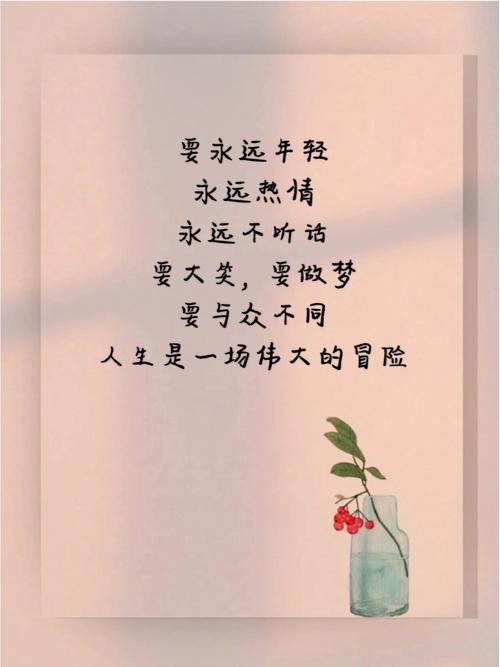
本文發布于:2024-03-24 23:04:26,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本文鏈接:http://m.newhan.cn/zhishi/a/1711292666171479.html
版權聲明:本站內容均來自互聯網,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上海城市空間重構過程中的記憶、地方感與“士紳化”實踐.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上海城市空間重構過程中的記憶、地方感與“士紳化”實踐.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